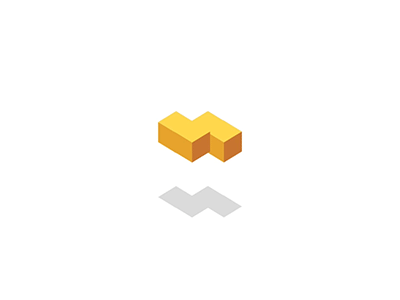一位先生的个性化生活
——著名作家石英记
宁新路
一个人每天要奔几十里地吃一顿午餐,且多年来风雨无阻地去奔这顿午餐,是这个地方的饭绝无仅有,是他在这城市无亲无故,还是他有什么特殊缘由?他有老伴和亲人,他有体面的收入,他有自己的家,他说不出赶这遥远午餐的特殊情况,但这午餐却成了他生活的必需,他每天非赶它不行。
这午餐不是筵席,是机关大锅饭菜,没有家的小炒好吃,他完全可以在自己家里做饭,完全可以在楼下的饭馆点菜,可他天天却去奔吃这顿午餐,连身体不舒服时也强迫自己吃食堂,变成了意志和体力的较量。他从退休后没有离开过这食堂,一直“吃”到如今的83岁。他说他的身体爽朗,食堂师傅不拒绝他,他仍将在这食堂吃下去,吃到哪天跑不动这食堂,就罢了。
这个赶午餐的高龄人,是著名作家石英先生;这个食堂,是人民日报社食堂。石英先生住在西城的南礼士路,报社食堂在东城的金台西路。住在城西的他,要赶城东的食堂,食堂大门按点开和关,每天得按时赶路,不得耽搁,过了点儿吃不上,那就白跑。这在石英先生来说,犹如去朝圣,每天的赶路,不敢懈怠,马虎不得。跑几十里路吃午餐,在京城作家中唯一,在京城老人中也许没有第二人。石英先生的午餐,就成了人们的好奇,也就成了让人不可思议的谈论。
石英先生独居在北京南礼士路附近的一座高楼上,总共30多平方米的一居小屋里,除了一张不大的床和书桌,一台电视和茶几,再也摆不下什么家具。身材高大的石英先生,与这窄小的居室,是那么不匹配。屋子难以容下第二个人住进,更是没有放女人梳妆台和大衣柜的地方;没有吃饭的餐桌,只能把茶几当饭桌;没有放沙发和多放一把凳子的地方,来客只能坐床头;没地方放书柜,书报只能堆在书桌和床边。窄小的厨房、卫生间阳台,刚好是一个人活动的空间,它“拒绝”过日子的女人。
石英先生在这小屋独居七年了,没有活动空间的屋子,他住得满心喜欢,床头挨着书桌,餐桌的茶几挨着厨房,上厕所几步之遥,倒也便利;微小阳台兼窗户的阳光,洒在书桌上,也洒在屋里,给这个斗室带来了生机,他写作时总能看到阳光和蓝天。他在这间小屋里生活、思考、读书、写作、会友,享受着一个人的清静世界,也享受着大多人难以接受的孤独的奇妙。
石英先生住在这般小的屋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他说,惬意而自在。他说这小屋出“活”。出“活”,就是能使他写作精力充沛,文章高产。他在这窄小的空间读书快而多,一天能写好几千字。他在这小屋写了多少篇文章,他自己数不清楚,却是从年轻时到现在,他已出版了七十多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惬意而自在,是石英先生享受着读书和写作给他的愉悦。他感受到了这窄小的空间,给他带来的难以形容的独静。
他这独静的享受感,我在多年前不大相信,以为石英先生委屈地在这小得可怜的屋里孤独地生活,是他人生的不幸和尴尬,绝对与快乐无关。因为他是四十年代战争年月参军且到地方工作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高干”。他有丰厚的工资收入,他有大而体面的房子,他有风雨同舟的老伴,他有关心他的两个女儿。他的高龄且继续往高龄上走的年龄,与老伴与孩子住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人之常情,他没有理由独居在这小屋里,就像旁人没法理解他而担心他安全一样,总感到他独居是个谜,也是很危险的事。别人的费解和担忧他清楚,可他从来没有搬回去的意思,他老伴也居然理解他的独居。老伴和女儿从不怀疑他超强的自理能力,也从不担心他身体出什么问题,他搬不搬回去住随他。除了他与老伴每周团聚一次外,他与老伴都习惯了各自独居的生活方式,且彼此已很自然。
当然他与老伴每天总有六七次频率的电话,聊天说地,互相提醒和关心着,虽比同在一起说话的时间少些,但聊起来也常放不下电话。尽管他的电话打频繁了,老伴嫌烦,但他动不动还会把电话给老伴拨过去,老伴就跟他聊。时常聊很长时间。
石英先生的午餐,自打他调入人民日报社那天起,就在那大食堂吃到了离休后的现在。吃习惯了食堂的饭菜,他总感觉食堂的饭菜好吃。也许是他吃这大锅菜吃出了深厚情感,也许是自我安慰。离休后的石英先生,完全可以回家吃老伴给他做的午餐,老伴也劝他年龄大了每天跑几十里地吃顿午饭太劳累了,可以自己做或回到家里吃,石英先生其实也不想去吃这遥远的午餐,他虽动摇过却没放弃。他如登山一样跋涉着,每天按时出门挤公交。去一趟来回赶路几个小时辛苦而费时,且每天上午十点钟必须坐在公交车上,还得给坐车堵车打出时间,否则就赶不到金台路,就赶不上食堂的饭,那就得街头下馆子,这使得他按点赶车,从不敢马虎。除了休息日他不去报社食堂,其他时间除非去了外地,都会风雨无阻地赶这顿午餐。为迈出家门,他通常是一条打起精神的腿,拉着另一条无精打采的腿强行赶路。
从北京南礼士路到金台西路路远不说,还得倒车,挤来挤去累上加烦。这累和烦与那食堂实际上不是多么可口的午餐相提,这顿饭与这劳累不成正比。在别人看来,宁可不吃这餐饭,也不愿受这般累和烦。所以,吃这般苦吃这餐饭这样的事情,在寻常人那里不可能发生,即使每餐饭倒给补助费也不愿受这般累。可石英先生似乎把每天赶吃这遥远的午餐带来的累和烦,当成了活着不能丢失的内容。放弃了这神圣的远行的午餐,好像生命的火焰就会很快熄灭。因而他把赶吃遥远的午餐当成每天神圣的一件事,无论什么天气,无论心情好与不好,无论身体难受与否,无论有谁好言相劝他不要为顿饭折磨自己,无论他给自己会找多少条不去的理由,他都会说服自己,甚至骂自己,让自己在痛苦时穿衣和背上那大包,催赶自己如时出门赶公交。当许多时候被他内心另一个想偷懒的石英即将把他“推”倒在床上和不让他离开温暖的屋子时,他就对自己发脾气:“石英,你这个懦夫,赶紧出门赶公交车……你要今天偷懒,明天也会偷懒,今后会随便找个理由偷懒,那你就会彻底变成懦夫!”
在这样艰苦的斗争下,总是懦夫的石英屈服,真正的石英胜利,那遥远的神圣般的午餐,会顿然在他眼前飘出香味来,让他顿生饥饿感,让他也顿添苦行远路的力量。所以,石英先生离休后多年来为吃这遥远的午餐,不仅要痛苦地接受赶挤公交车的劳苦,还要为每天甘愿受苦吃这顿午餐做不断的精神斗争。要化解掉这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不那么简单。因为下雪、下雨、刮风、酷热和身体不舒服时,会有十二个不出门的理由;因为他那虽小的厨房,米面油盐和锅碗瓢盆齐全,楼下卖菜,可以自己做饭。他会做可口饭菜,即使不愿开火,下楼就是美味的餐馆,那餐馆里有他最爱吃的饭菜,吃一顿饭花不了几个钱。但他想到这些省事的借口时,仍然是把自己骂出了门,强迫自己赶往公交车站。在这样一种与自己不停地较量下,每天的赶路吃食堂,渐成他心里庄严的出行,变成了他一天生活不可缺少的赶路,更成了他保持生命力旺盛和追逐健康活着的心理渴求。
当然,石英先生赶吃这遥远的午餐,还有一个缠绕他每天不得不去报社之事,那就是不断的邮件和稿费单。几十年来做编辑和作家,尤其是成为著名作家后,邮件和稿费越发渐多,他的小区没有邮箱,重要邮件收不到,也就只好由报社收发室继续代劳。这也是他被每天“牵引”到金台西路2号的一个缘故。
独居成一种享受,如何把孤独与寂寞变成习惯且不觉得孤单和凄怆,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到的,需要让老伴和女儿接受,也得有战胜寂寞的强大毅力。石英先生和他的老伴,都能接受这种孤单,且不觉得它是孤单和寂寞,是有生活根源的:石英先生年轻时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他在天津,妻女都在北京,分居成了他与老伴的生活习惯。独居惯了的石英先生,写作需要安静的地方,就住在了女儿空闲的这蜗居里,感到写作出“活”既快又多,且一个人的安静让他有了享受的感觉,便也就一年年独居了下来。他每周六回家与老伴团聚一天,下午回到自己的小屋,每周如此,他同老伴都没有了不自然。石英先生独居,反而成了全家自然的事。家人看他独居精神爽朗,身体健康,著作一年几本出版,身心和精神状态很好,他不愿搬回来住,也就由着他了。
石英先生遥远的午餐和独居的生活,构成了他独特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养成了他个性化生活方式,他与在一个都市的老伴每天亲切地电话聊天,与有闲的女儿亲切地电话聊天,国外定居的女儿每周给他打一个问候电话,他每周抽一天上午的时间欢喜地回家与老伴相会,下午回到自己的独居室,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仍每周五天赶吃报社食堂。石英先生这苦行僧式的生活,写文章之多令人羡慕,且八十多岁了腰板直得像树干,脸色红里透白,走起路来铿锵有力,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精气神旺而不虚,这倒是让人有了点猜想:石英先生遥远的午餐和寂寞的独居,莫非对他的创作和健康,很适合;这苦寂的生活,是他创作的营养素?石英先生笑而不答这个问题,而他的笑却回答了这问题。
--------------------------------------------------
作 家 简 介

宁新路 当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转世天狼》、《财政局长》、《艾先生的个人烦恼》和长篇散文《来去无尘》、散文作品集《近处的风景》《人在西阳里》《朝着阳光走去》《相思树》《阳光照到星期八》《会笑的云》《熟悉的陌生人》《别把阳光浪费了》《误入热地》等共17部。供职于财政部中国财经报社,《财政文学》主编、高级编辑。中国财政文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长篇散文获第26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散文获第五届“中国散文冰心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奖大赛一等奖、第二届中国报人散文奖等数十项文学作品奖。十余篇散文被选入中小学试题和复习教材。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曾为武警中校,武警部队总医院政治部宣传文化处处长。5次荣立三等功。2001年转业到财政部,在中国财经报社总编室和新闻部、中国会计报社等任职。曾获财政部“五一劳动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