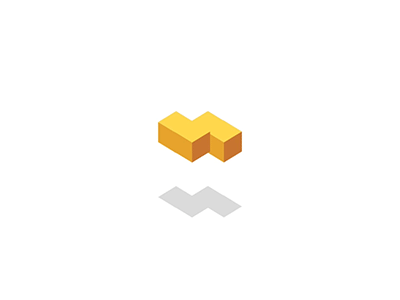五月下旬来西安,陪老作家周明到他的老家周至玩了一天。周至此前去过两次,对楼观台仙游寺印象很深。近些年,周明对仙游寺钟爱有加,光他邀写的各种名人书画就有上百幅,如赵朴初、冰心、周而复等人。看着那精彩纷呈的碑林上的字迹,我对周明说,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在这里写下千古奇文《长恨歌》,今天您又帮助完成了书法碑林,真应该给您和白居易立两个塑像。周明说,给白居易做个雕塑是应该的,咱是小人物,微不足道,如果我百年之后,倒是愿意长眠在仙游寺。我一听笑了,说您这身板活120岁没问题。
西安出画家,也出雕塑家,更出无数大大小小的文人。毕竟是十三朝古都之所在啊!我在西安居住期间,当地的许多文友三天两头拜访,偶尔也到他们的工作室闲逛。在全国,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个城市的文人有如此多的工作室,如果我用星罗棋布、遍地开花形容,你肯定觉得夸张,可是,当你置身长安、曲江、西咸、高新、周至等新区的楼宇、村庄、山林中,确实会看到景色各异、装修奇葩的工作室。
想来,人们为什么要建工作室呢?工作室源于我们过去所说的书房,书房不等于存书的库房,他是文人写字画画接待朋友的地方。书房相对于客房、相对于主人的卧房是有机的组合,这当然取决于主人的经济实力。在古代,有书房之人,大多为官宦富贵人家,老百姓是很难做到的。对于更多贫穷的人家,他们所处的往往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现在,生活富裕起来的人们,有了宽绰的住房,甚至有了多余的房舍,在内心浮躁时,特别需要一个舒适安静弥漫书香的环境,与其说建一所书房——即所谓的工作室,倒不如说给自己建了一个养生堂。
国庆节,闲呆在酒店看书。忽有文友打电话约我到终南山,说见一个奇人。我说,在终南山修行的人很多,几乎各个都是奇人怪人。朋友说,那是一个画家、雕塑家,你见后一定喜欢。于是,我们驱车直接奔向终南山。到终南山我首先想到的是终南捷径这个词。我知道这个词多少带有嘲讽之意。是呀,读书之人,修行之人,谁不想被帝王发现而平步青云呢!可我也相信,有个别的文人、高士他们到这里也确乎是真正的为修行而来。
汽车蜿蜒了十几里山路,停靠在一座不大的农家院前。透过竹篱笆,几棵松树间掩映着一排老房子,院子里种植着些许斑竹。我问接待的女主人容阳,过去听说秦岭时有大熊猫出没,不知这里可有?容阳参禅般的回答我,那就看你的造化了。说完,她就领着我们到房前屋后去参观。农家院落过去看过很多,但像这个院子里到处陈列着各种雕塑品的并不是很多。我问,这是哪位艺术家的作品?一同前来的张焕军笑指容阳,那个艺术家就是她先生周起翔。
周起翔?我隐约好像听周明跟我提起过。我问,就是为司马迁、于佑任塑像的那个雕塑家吗?容阳说,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们家周老师。我用惊奇的眼光看着容阳,从容阳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是很以他们家周老师骄傲哩!我不禁迫不及待的问:周老师在家吗?容阳指了指三楼说,他现在就在工作室画画。
按常理,朋友来了,主人大都要到门口相迎。可周起翔不会,他通常早晨五点多就钻到工作室读书作画。容阳说,她特别理解周老师,这几十年,她觉得周起翔一直活得天真、纯粹,他的脑子里永远装着他的艺术。为了雕塑司马迁,他反复研究有关司马迁的史料,甚至效仿司马迁把自己关在一间如牢房般的黑屋子里几天不出来,几乎饭也不吃,在那个似乎忘记时空的密室里,他默默地与司马迁对话,问及到心灵深处,他竟然嚎啕大哭。在雕塑司马迁初稿时,不知什么原因,从司马迁的脸上突然掉下一块泥巴猛地砸到他的脚上,他抬头一看司马迁的受伤的脸,好像让他想到什么,竟然一下抱住司马迁又一次失声大哭。“我知道,那一刻周老师和司马迁的精神世界是真的打通了!”容阳动情地说。
徜徉在周起翔的艺术工作室,欣赏着他一件件雕塑作品,一幅幅水墨画,我对周起翔说,你这里四面环山,真是世外桃源,别人来到这里是为了修身养性,难不成你是来雕塑大山的?周起翔说,他从小性格孤僻,天然喜欢一个独立思考问题。每当夜晚,他常常一个人沿着门外的山路往深处走,那时的山里除了泉水叮咚作响,再也听不到其它的声音了。我说,那您不害怕吗?比如遇到毒蛇、豺狼、野猪什么的!周起翔说,人和大自然一旦统一,就谁也不是谁的敌人了。他最初来到这里,猫头鹰每天都在树上叫,轰都轰不走。后来,他终于明白,是人类占了鸟的地盘,所谓不平则鸣,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时间久了,再也听不到猫头鹰的叫声了。
我很想跟着周起翔去看他一天是如何为人物雕塑的。容阳说,他前年9月曾跟着周老师到长安探班。那天,他们早晨5点起床,6点就开车奔长安的工作车间。大约7:30分,周起翔就穿上工作服开始为医圣岐伯塑像。容阳在日记中写道:他爬上了五六米高的雕塑架,打开了保护膜,歧伯的和善面容露了出来,他上下穿梭,一会儿拿起锤子敲打,一会儿拿起刮刀雕刻,一会儿又抄起魔棒上下调整,动作之轻盈,手法之娴熟,完全忘记了自己已是62岁的年龄,更是顾不得我的存在,到了这里如同到了他的主战场 ,如鱼得水,没有片刻停歇。我感叹自己有力使不上,有忙帮不上,有看的份,没有插手的劲。随即拿起了相机,记录下了这生命长河里跳动的旋律音符,那个小小的音符在这并不华丽的五线谱里显得那么清脆动听,令人心醉。
在陕西或者说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中,于佑任是非常重量级的人物。周起翔应邀为任公塑像,其压力不亚于为司马迁。在陕西知道了解于佑任的人很多,人们通过影视作品、文献资料都看到过先生的形象。如何塑造一个形神兼具的美髯公,无疑给周起翔出了个难题。就一般的雕塑家而言,把人物塑造成形似,并不是难事。但周起翔却坚持,艺术最值得人们记取的不是作为艺术品的物,而是它给人的启发。周起翔是个有思想定力的人,他经过冥思苦想,最终把于佑任塑造成了一个伟大的爱国的思想者。2010年,于佑任塑像塑成后,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的轰动,许多人从四面八方赶到于佑任博物馆参观。这其中也惊动了远在台湾的于佑任的儿子于中令,这位已然七十多岁的老人辗转来到西安,当他来到父亲的塑像前,一下子被惊呆了,然后猛然扑到父亲的身上掩面哭泣道:这就是我真实的父亲啊!于中令当即请有关方面要尽快找到周起翔。周起翔和于中令的见面可以想见是激动人心的,他们一起谈于老先生的轶事,谈浓浓的乡情,本来约好只谈四十分钟,结果谈了两个多小时。于中令感动之余为周起翔写下了:“山巅高渺望乡讯,天际苍茫铸国殇”。
人们常说艺术家都有精神怪癖,周起翔也不例外。在农家院三楼阳台,他一个人常常发呆,即使容阳从他身边走过,或者喊他吃饭,他也视而不见听而不予。在工作室,最能与他交流的常常是小白狗和小花猫。当下,很多人都关注艺术家作品的收入,我也毫不掩饰的问了周起翔这个问题。周起翔倔倔的对我说:“我不是商人,我的作品只卖懂我的人。”容阳插话道:”周老师只钻研他的艺术,不善于与人打交道。来了朋友,如果说得来,他会同人聊上大半夜。如果谈不拢,他会当即拒绝,哪怕是比较重要的人物。”
离开农家院时,天空飘落起小雨,容阳问我们带没带伞,周起翔则在细雨中捋着他的长发向我们挥手。这时,我想到刚来山庄问过容阳的话——这里有没有大熊猫出没?现在我豁然开朗了,这里当然有大熊猫,只不过其“人在山中不知晓”罢了。
2021年10月6日西安故乡润土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