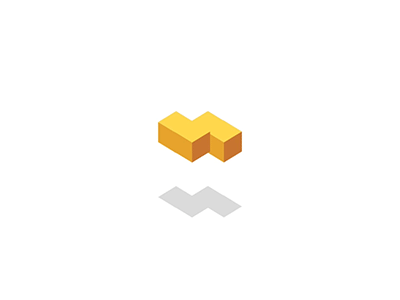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


公元1966年夏,毕业考试后,正准备报高中志愿,“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瓢凉水从天而降,浇灭了我心头升学的旺火。同学们全部投入“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学业停止,报考“包一中”的梦想破灭,前途渺茫。命运就定格在“老三届”“六六届”的标牌上。
开头以为运动几个月就过去了,没想到一发而不可收,越闹越凶猛。课本和书籍都被当作“四旧”破除,我只能在“大不理解”中随大流运动。
不久,“出身不好”的学生全被划为“黑七类”,从各宿舍中清除出来,统一安排到原来做仓库的石头窑洞中,十人一家,由二名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管理。看着听着人家趾高气扬、发号施令,心中暗暗叫苦的同时,还有几分羡慕和嫉妒。
“黑七类”子女上午打扫校园、厕所,下午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文章。我被选为“读者”,给大家读“红卫兵”指定的篇目。几个小时下来,口干舌燥,头晕目眩。学习完毕,别人去食堂吃“份饭”,我和一个姓白的同学因家庭贫困只能自起炉灶,把从家里拿来的小米土豆熬成粥喝,聊以解饥。每星期回家一次,步行往返七十里山沟土路,背上十几斤粗粮、土豆、萝卜充当一周食物。不能回去就由二弟送来。往往是星期五就断炊,手捧红宝书,饥肠碌碌接受改造。
我很想家,想那个大青山深处小山头向阳面的土房子,那里有我的父母弟妹,他们在穷困窘迫中过着纯朴的农家生活。父亲在“三年困难”期间自愿申请退职,由一名国家正式教师变成民办教师,“文革”开始后,造反派以“成份不清,有历史问题”为名停了父亲的职务,。“监管”务农。母亲自然脱不了干系,陪着劳动改造,料理一大家人衣食生计。我想回家劳动减轻父母的负担,他们不同意,劝我“服从学校的安排,不要放弃学业”。
秋天,从北京来了几个“红卫兵”,到我所在的包头第十五中学煽风点火,成立了“革司”、“红司”。我当然被拒之门外。除了集体劳动学习,我就反复读《毛泽东选集》(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而《毛主席语录》则不离身,到了背诵的程度。另外,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上下册《鲁迅选集》有空就读,虽然纸黑有些还字迹不清,但我很喜欢。还把写大字报的色纸裁成32开订成本子,摘录其中精彩的句子。
入冬后一个周末下午,“红卫兵”组织要我们十几个“黑七类”把从老师家里抄出来的旧书集中到操场上焚烧,我边搬边看,有很多中外古今名著,象废物一样推成一大堆。他们点火燃着表面后走了,命令我们几个人看着,等烧完就可回家。我眼光发瓷,浑身颤抖,心哭无泪。不大一会儿刮起大风,西北面黑云翻滚,遮没了太阳,雪花飘下。着火的书堆火势大发,灰飞纸扬,朝东南的教室扑去。我让伙伴们赶快用铁锹铲土压火,以防引起火灾。
雪越下越大,黄土伴雪一会儿就把火压灭了。我让他们几个先回去,自己再守一会儿。人走后,我赶忙用锹翻开被湿土压着的还没有烧化的书籍,有十几本贴地的完好无损,其余的半焦残黑无法辨认。我返回宿舍,拿起装小米和土豆的布袋到操场,将烧剩下的那十几本书装好,向北走上回家的道路。
回到家里,父母弟妹们已熄灯睡下,我拿上油灯火柴,提着布袋里的十几本书钻进对面阴坡上储存土豆的窖里,点亮油灯,把书埋入土豆下面。
校园有墙处全贴着大字报,有的地方已覆盖数层。揭批“牛鬼蛇神”教师,揪斗校长、教导主任,参与区里批斗“走资派”,忙得不亦乐乎。各种“战斗队”、“司令部”粉墨上台,你方唱罢我登场。
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子女只能冷眼旁观,反倒多了几份沉思与反观,说不上理性思考,但也犯不着极左与狂热。年底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学毛选小组”,一面以毛泽东思想改造主观世界;一面也想用经典指示解读运动、预测前景。这些初衷被打砸抢、武斗等乱象彻底搅浑,“革命造反派”用自己的行动不断颠覆着他们敲锣打鼓欢腾宣传的“最高指示”。
那年代,在集体无意识的旋流中,不可能理智操控自己的命运,只好随波逐流。倒是给我这“出身不好”的人很多读书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