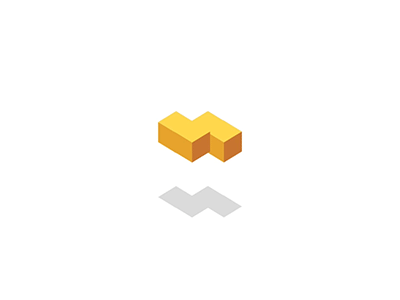秋高气爽,雁过留声,瓦蓝蓝的天上没有一丝云彩。
昨晚就和二弟商量好,今天和他去戽鱼。二弟不喜欢吃鱼,但对戽鱼特别有兴趣。今天天气好,所以心情也好,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俩别提多兴奋了。
戽鱼地点就在家西边水稻田的条排沟。前几天,在这块水稻田里,我和二弟在平水缺口的小塘里和不远处的脚塘里,没花多大功夫就捉了几斤刀子鱼和小鳊鱼。现在水稻即将成熟,管水员赵长友大爷也有几天不来放水了,田里的水早已干枯,唯有条排沟里还有大半沟水。我记得那时候稻苞虫结了“角子”,纵卷叶螟造成白叶、卷叶了,也不知道打药水,中尧队长就安排几个社员用竹子做的一种长柄的梳子在秧叶子上面来回梳。参加工作以后我才知道,这种做法其实都是放的是马后炮。因为不打药水,所以沟里鱼非常多,而这个时候正是戽鱼的最好时机。
早饭后,我和二弟就忙着收拾铁锹、脸盆等工具准备去戽鱼。没有箔子,正准备把窗帘拿下来,正好被祖母看见。所谓窗帘,就是用芦柴和草绳编的,祖母有的舍不得。经不起我们花言巧语,又再三保证,她终于同意。看到我们扛着铁锹拿着帘子等工具飞奔而去的飞尘,她迈着圆规似的双腿和小脚,柱着根破竹竿,颤颤巍巍地追在我们身后,对着远去的身影啰哩啰嗦重三倒四地大声叮嘱,千万不要把窗帘弄坏了啊!
祖母不放心帘子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窗帘和门帘都是今年她新编的,花了许多功夫。编帘子的工艺並不复杂,借的廷选大爷家的“帘机子”(就是五六尺长、膀子粗细、上面有刻度的木棍)。编织时,“帘机子”用两根绳子吊在斜放墙上的木棍上,用帘子长度三倍左右的茅草绳五六根,每根绳的两头扣两个半截砖头,将绳子绕一部分在砖头上,然后放在有刻度的“帘机子”上,再将切好的、帘子宽度的芦柴拿一根横放在“帘机子”上,拿起前面的砖头到后面来,后面的砖头拿到前面去,使绳子勒在芦柴上,依次来回拿过去后,再拿一根柴,方法如上,前后拿砖头编。因为今年编帘子的柴和茅草都用完了,要到明年才有,所以,整个秋天要是没有帘子,蚊子“夯天”(方言,到处飞的意思)的日子真难过呢。
来到条排沟边,我和二弟商量,因为沟太长,我和他分开来戽,一人一段,看谁戽得快,鱼戽得多,二弟便同意了。接着我俩开始打坝,东西长的沟有几十丈,沟中水也不是太深,我俩在中间地段的沟两边,用铁锹挖沟边带草的泥土打坝,不一会儿坝就打好了。其中东边短些,我让给二弟;我是哥哥,力气大些,就戽西头长些的一段。我心里暗想,长些的这段鱼肯定要多些。
接着开始准备戽水,为防止把衣服弄湿弄脏,我俩干脆脱掉裤头,光屁股站在沟里戽水,我用的是搪瓷的脸盆,二弟用的是铜脸盆,一人一头开始戽水比赛。他光屁股朝月亮往东边戽,我光屁股朝太阳往西边戽。
尽管我的沟段面比二弟的长些,因我力气大些,又用的是大脸盆,不一会儿沟里就剩小半沟水了。鱼是跟水走的,开始的时候水深,鱼听到水响不敢来,现在水少了,为防止把鱼戽岀去,我拿来窗帘当箔子插在离坝两三米的地方,箔子两边又用烂泥垒起小坝。
俗话说,吃鱼没有取鱼乐。想起前几天在稻田捉鱼的快乐情景,又想起今天的鱼是前几天的许多倍,就像渔人在雾海中望见了灯塔,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小鸡啄食似的撅起屁股朝天戽得更带劲了。
看到水渐渐地浅了,趁休息的功夫,我想看看鱼多不多。按以往的经验,这时箔子周围应该有鱼在欢快地跳跃了,我转身看了看,一点动静也没有。心想,也许鱼在东段呢,又使劲戽了一会,沟里的水已剩两寸左右了,回头又看了看,箔子周围一条鱼也没有。我有些不淡定了,扔掉脸盆爬上田埂上来,睁大眼睛,扫描般沿沟边朝东看去,只见浅浅的沟水清澈见底,比玻璃还透明,连一条火柴棒大小的鱼也没有。心有不甘的我,又从东头“泮”(方言,走或趟的意思)到西头,心想也许有些大鱼在脚塘或淤泥里,边走边用两手在淤泥里摸来摸去,这就奇了怪了,仍是一无所有。这沟两边稻田有七八亩,前几天只是在北边一块平水缺口附近捉了几斤鱼,还有许多鱼难道飞了不成?戽了这半天功夫,早已筋疲力尽,早上喝的两碗稀粥也早已跟尿走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气极败坏的我拔起箔子,用大锹叉了个稀巴烂。
二弟见我叉箔子,忙过来看个究竟,见没有鱼,也觉得奇怪,边对我说,哥,你到我这边来看看,我这边鱼多呢。
再看二弟这段,只有我三分之二的长度,由于戽得慢,水比我这段还深些,只见由东到西的沟里,满满的都是大大小小的鱼游来游去,有刀子鱼,有鳊鱼,还有昂刺鱼,“惨”子鱼,泥鳅等等,挨挨挤挤,有的在水里翻着泡泡,有的被拥挤得跃上水面;还有青蛙、蛤蟆等跳来跳去,热闹极了。鱼知嬉水之乐而不知人之乐,兴奋的二弟又骄傲,又乐滋滋地对我显摆说,你看我这边鱼多吧,今天你输了吧。也许是期望值过高的原故,也许是强烈的妒忌心和好胜心,让我在二弟面前输了面子又丢了里子,使我失去了理智,这咅萨老爷他妈的也太不公平了,同是一条沟,刚刚早上打坝分开戽的,我这段鱼没有也就罢了,居然连个蛤蟆都瞧不起我。顿时火冒三丈,跳到沟里用手扒二弟戽水的这边小坝放水,说时迟那时快,坝已被我扒开了碗大一个缺口,水哗哗地流向快要见底的沟里。二弟先是一愣,见我气呼呼地使坏,连忙跳下沟来护坝,又大声哭喊着,奶奶快来呀,没得了了,哥哥放我的坝了。见我不理他,又对我求饶说,好哥哥,好哥哥,你不要放坝,今天戽的鱼全归你行吗?边说边用身体挡我,不让我扒,又用手挖泥垒我扒的缺口。
这时,闻声赶来的祖母听了二弟的哭诉后,看到我俩光屁股满身泥浆,就像两只掉在“牛汪”里的泥猴子,特别是看到被我叉烂了的窗帘,气得她立刻脸拉得老长,挥着破竹子拐杖使劲打我,撕心裂肺地骂道:你个上炮轰的,你屎拉不下来怪马桶,戽不到鱼帘子又关你什么事?老二戽鱼关你什么事?你放老二的坝干什么?你行什呢阴决啊(使坏的意思)?你个砍千刀的,打死你个砍千刀的。随着祖母连珠炮似的怒吼,她手里的破竹拐杖像连枷一样打来,我防不胜防背上挨了一下,立马光着屁股连滚带爬跑了好远,直到我没了影子,空气中还断断续续飘来祖母咬牙切齿沙哑的声音,你个砍千刀的,把好好的帘子叉了,你不要回来,没得中饭把你吃……。
至于后来那天午饭究竟有没有吃,什么时候回家穿衣服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就像煮了一锅的破饺子,糟糕的心情荡到了谷底。
那一年我十二岁。
2020.6.27于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