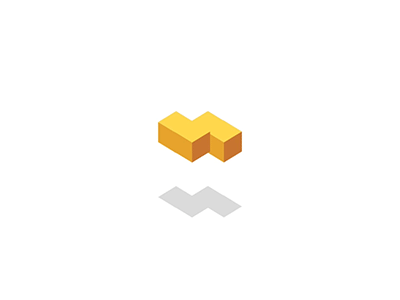记得2009年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陈平原教授在题为《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的文章(《读书》2009年第9期)中梳理了1949—1999间五四运动逢十周年庆的主流报刊概貌。他以“关键词”的形式提炼了这五十年间的言述脉络:
一九四九年:革命路线
一九五九年:思想改造
一九六九年:知识分子再教育
一九七九年:解放思想
一九八九年:体制改革
一九九九年:振兴中华
然而,在2009年主流报刊的纪念文字里,我们已经很难提炼出这样的“关键词”,关于“五四”的纪念,已经变成像这场运动本身那样众声喧哗(参见《话题2009》)。
说起“五四”,一般人心里都会有两种印象,一种印象是“还我青岛”的旗帜,赵家楼的火光;另一种印象是《新青年》打倒文言,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以及林琴南盼望有个“伟丈夫”来扫除这帮子新文化人。
不管胡适晚年多么强调这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两场运动,前者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但平心而论,这两场运动之间,内在的逻辑是相似的。
今年是“文学革命”100周年,文学革命发动的标志,正是1917年的两篇文章: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两篇文章的激烈程度相差甚远。偏爱传统又主修西方文学的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平和地叙及《文学改良刍议》,却大肆吐槽《文学革命论》:
紧接着《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的下一期,他就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给胡适捧场,内容泼辣,文字浮夸异常。陈独秀这篇文章,以文学知识和立论态度来讲,真可谓集无知与不负责任之大成,其精神上和胡适那篇劝人不要用陈腔滥调,不要作无病呻吟的文章可谓背道而驰……列举了这三大主义以后,陈独秀就把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作一个简短的、流水账式的交代,说中国文学一向是操纵在迂腐而晦涩的贵族文学家、古典文学家和山林文学家的手里。
但从文章的传播效果来看,正是《文学革命论》而非《文学改良刍议》给了《新青年》的主要拟想读者——青年学生与旧文学家以极大的刺激,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也将“新旧之争”变成了一个社会话题。
此后的“王敬轩”双簧信,以及《新青年》上一系列的通信,用今日传播研究之眼光视之,毫无例外都是“炒作”。想当“舆论家”的胡适不赞成搞“双簧信”这种不够光明正大的手段,他主张“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种平等讨论的主张马上遭到陈独秀激烈的驳斥:“白话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新青年》3卷3号,通信)
更狠的论述策略是五四运动前《每周评论》刊登《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搜集了五家报纸对于“北大驱逐教员”谣言的批评。但是这五家报纸并未将此谣言与林纾等旧文学家联系起来,只是指责“今之当局者”。
但陈独秀在文后的按语中称:“这班国故党中,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新申报》里《荆生》的著者林琴南,和《神州日报》的通信记者张厚载两人。”一个月后,他更是直斥:“林纾本来想借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那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作主。他老羞成怒,听说他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新文学后来取得了主流地位,像《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这样的史著就会直接写道“林纾等人散布的北大驱逐陈独秀、钱玄同的谣言”。
其实,林纾写《荆生》是洩忿不假,他后来道了歉。但迄今我们都没有任何证据说他散布谣言,或向当权者乞援,要借助政治势力来压制不同的文学观点。倒是新文化阵营通过这种叙事,成功地塑造了自身“受难者”的形象,在此后的论争中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五四运动的内在逻辑其实也一样。五四运动的肇因,一般都说是来自巴黎和会的负面消息,然而中国此时的外交态势,是否真是严重到“亡国”的地步?这是可以讨论的,至少不会比日方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更严重。而罗家伦在回顾五四运动的成因时,提出过四点,“巴黎和会”只是其中一点,而且主要不是亡国的危险,而是“感觉到中国受人支配和帝国主义国家协以谋我的痛苦”。另外三点原因,一是以前学潮的惯性,二是新文化运动带来思想变化,还有一点,是蔡元培的影响:以前是羡慕官僚,现在是鄙视官僚军阀,而且想着“有意去撄官僚军阀之锋”。
因此,与其说五四运动基于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不如说它是由积蓄在“新青年”内心的激愤与沉痛引发的。当然,一场群众运动一旦发生,会远远超越它的初衷。五四运动在近代史上的影响之大,是由很多别的因素决定的,包括各派政治势力对青年群体的争夺,等等。
更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内在的逻辑充满了矛盾。比如说:一方面,陈独秀及《新青年》同人都在不断强调说青年应该独立地思考,应该“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强调的是在价值抉择中,必须要经过一个理性思考和判断的过程,这一表述看起来很能够代表新文化运动对理性的强调,但是他们的实际论述中,却存在着明显有悖理性要求的状态。新文化运动一出来,就必须要用一种新的文化来替代旧的文化,它一开始就并没有给大家留下理性地、独立地思考旧传统并做选择的余地,它更多地是要让你把旧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并做一个整体性的否定。比如说像一般人比较熟悉的“桐城谬种”啊,“选学妖孽”啊,“十八妖魔”啊,“孔家店”啊这样简单化的命名或者说批判,事实上就要求大家在新旧之间划出一道绝对的鸿沟,在新旧之间形成绝对的价值落差,即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差的。
《新青年》呼唤的“新青年”,是独立的、不受别的思想阻碍的、不受任何外在环境限制而独立进行思考判断的青年,但是《新青年》传输给当时青年的思想却是:你必须要对旧的传统产生一种偏激性的愤恨,因为只有在这种愤恨之下,人才可能彻底地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前者是《新青年》的显性诉求,后者是它的论述策略,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矛盾。
蔡元培与陈独秀
再比如,蔡元培提倡的“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听起来兼顾两者,但实际操作其实连蔡元培自己都很为难。因为他一方面将来自巴黎的警报通知学生领袖如傅斯年罗家伦,一方面又亲自在北大校门阻止学生游行;一方面竭力营救被捕学生,一方面又对蒋梦麟担忧“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而傅斯年在1919年10月底的回顾中引朋友的话说:“一年来我们全国青年学业的牺牲,其总数不止一个青岛!”
略显反讽的是,新文化阵营在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的历程中,建立的是受当局打压、被官僚迫害的“受难者”形象。但新文化运动建立日后影响、成为文化主流的最重要途径,却是1920年通过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教材改用语体文。不要说这时新文化已经取得大众认同什么的,这一年中国图书市场的超级畅销书,还是用骈体文写成的《玉梨魂》。
12下一页
来源:查字典文学资讯网 https://sanwen.aiisen.com/zixun-904/更多资源请访问:查字典文学资讯网 https://sanwen.aiisen.com/zix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