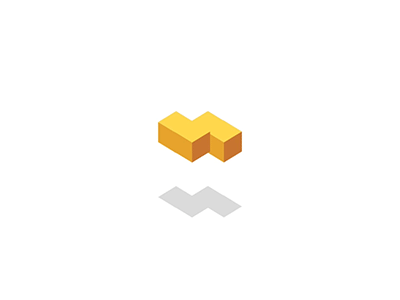在文学研究范畴里,解读文本向来有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不同路径。前者偏重语言、修辞、形式等所谓“作家作品论”,后者偏重文本的社会与政治属性,晚近学界对这个路径的偏爱是不言而喻的。
有些较为传统的学者将文学的外部理解称文学的功利性,而内部则呈现为非功利性。这样的解释或许可以自圆其说,但其实还是把所谓的“纯文学”的概念不加批判地便拿来使用了。其实,在严谨的思考中,任何命名都是需要慎之又慎的,做出定义乃至标签化,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而,严谨的写作者,在使用每一个概念的时候,都会从学术谱系上寻找她清晰的定位,而所谓“功利性/非功利性”的说法并不严谨,会有以偏概全、含糊定义之嫌。
不过,不可否认,文学的外部属性,追溯根源,在最古老的人类记忆里,就体现在对社会风俗、世道人心的教化中。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中,“教化论”与“意象论”是两大主线,而提倡改良社会风俗、教化人心是文学的社会功效之表现。
《毛诗大序》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典论·论文》更是直接说明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种对社会、政治风气的引导作用,也是文学功利性之所在。而白居易所谓“文章合为时而做,歌诗合为事而作”更是体现了这一点。直到晚清梁任公主张以小说之力量改造社会、促进民族现代性转型,“教化论”在中国文学上的作用达到了顶峰。
然而,如果单单是“教化论”,文学之外部属性未免太过教条。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的外围界限被不断泛化,借助意识形态批评,彻底改变了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被广泛甚至滥用的概念,其本来面目反倒被人遗忘了。
法国学者特拉西在《意识形态概论》中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后被马克思纳入唯物主义的范畴,又经西马大师们的改良,使之进入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中。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学的外部属性在这里加强了文本内外部的联系,让文学走出狭隘的心灵世界,成为勾连社会风俗和内在情绪的桥梁。
阿尔都塞曾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的说法,意在指出我们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社会政治的紧密联系。而目前依然活跃在西方左翼学术界的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干脆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说:“在第三世界的文本中,甚至那些有关力比多的叙事,也是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反映。”对于勾连“文本—文化”“修辞—政治”,文学的确显现着它的功利性,也是外部属性对文学内部的重新“打开”。
人们生活在一个“语言的牢笼”里,不断被阐释的概念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与想象。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的功利性最终为“文学”这门学科打开了更广阔的理论空间。
具体到文学批评上,比如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讨论赵树理与共和国文学新范式的关系,分析革命历史小说对“民族—国家”想象之作用等。这种“再解读”的方法借助的便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路径,如果按照“纯文学”的看法,这样做似乎与文学并无太大关联,但它们的魅力却是远超所谓“纯文学”的。在西方,福柯、马尔库塞、萨特等人早已不拘泥所谓“纯文学”的审美意象——讨论文学之外延,本身就是一种进入社会批评的渠道,而在这个意义上的“文学”,更近于“文化”。
于我而言,看待文学作品和现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而是一种跨学科的思维的综合训练。但也应看到,仅从外部属性来看,文学的功利性一方面打开了文本局限的视阈,但却容易走向消磨文学理论边界的另外一个极端。文学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康德所谓“美是无目的性的合目的性的”。用整体思维取代局限思维,从内部研究走向外部研究,指向超出文本但应植根文本,或许才是比较严谨的思考路径。
12下一页
来源:查字典文学资讯网 https://sanwen.aiisen.com/zixun-915/更多资源请访问:查字典文学资讯网 https://sanwen.aiisen.com/zix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