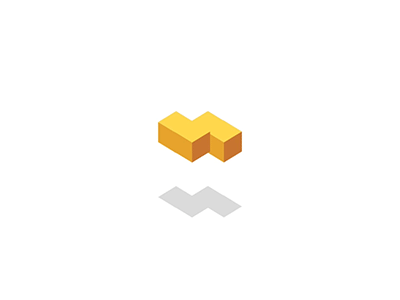亲爱的钓友,虽然你我素昧平生,天涯海角。但水为舟,鱼为桥,我们是朋友。感谢苍穹,感恩生活,我愿拉几颗粗糙的文字钩回匆匆的脚步,滚滚的车轮,冲锋的小号儿。光阴荏苒,水到深处,情到深处。问苍茫大地,江河湖海,人间多美好。
一、我要照相
沐浴璀璨的阳光,豪华的游艇拨开水面,将欢呼雀跃的孩子送到侧面的小岛上。
“噢,今天是儿童节。”
对钓鱼人来说,一年四季,无所谓节不节的。只要能坐在水边,只要能远离喧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看看高天的流云、地上的草、近身的竿漂、远处的鸟,便天天都在过节。
忽然,一群初中生跑过来。“叔叔,我们想借您的竿做背景,照相。”( 文章阅读网:sanwen.aiisen.com )
我应道:“有创意,尽管照。”
初中生们热闹了一阵,喊了一堆“茄子”走了。紧接着,红领巾们又蝴蝶似地杀将过来。“老爷……爷,我们也要……照相。”
“真没招儿,眨眼功夫我就升辈儿了。看来差几个年级真差不少。”
记得当年,自己戴红领巾入队宣誓也是在水库。天边峰峦叠嶂,衬托蓝色的湖面,我们弯曲手臂,齐刷刷向鲜艳的队旗庄严敬礼,红旗飘飘。只可惜那时没有相机,天真的红领巾沿水边排开,俯视水中的“我”,莞尔一笑,相就照过了。大约就在那年,一个从城里来的小伙儿,向本村的陈老爷子问路。告别时,小伙儿掏出半导体,说要给老爷子照相做个纪念。老人摆正姿势,憨憨的,小伙儿随“咔”地一声拨了开关。
想到此,我便高声说:“照吧!孩儿们。竿不够,爷爷再支几把。”
二、孙哥哭了
天刚亮,孙哥就把海竿抛了出去。他人长的高大,竿大、轮儿大、钩也大,握紧的爆炸食有鹅蛋大。
第一次去大水库开竿,又是初钓,甭提多兴奋了,那才叫水宽凭鱼跃、天高任人抛。用钓鱼人的话说,啥情况都会有,没准儿撒尿功夫竿子会被鱼拖走。
起风了,浪涛拍岸。朝前望去,烟波浩渺,海一样。同来的老钓友久不见动静,纷纷起竿“搬家”了。唯独剩下孙哥在原地死守。不知过了多久,他发现线松了,弯弯曲曲的。“不对呀,开始是紧的。估摸是浪打的。”随即又摇轮紧线。可不一会儿线又松了。
“换食儿!”他猛一提竿,咯噔一下,焖住了。“糟了,挂钩。”稍一喘气,发觉竿稍又向下沉,他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身板儿挺得老直,竿子绷得老紧,轮子收得哗哗的,而水下的东西就是不见面。他心想,鲁智深同志能拔垂杨柳,咱老孙他妈鱼还拽不动,不信邪呢!
鱼,终于露面了,那脑袋足有洗脸盆大,黑乎乎的。孙哥这下真的有点儿蒙,鲁智深的事儿早没影了。左顾右盼,不用说人,连雀儿都没有。他只好捧着竿一步一步向后退,鱼一尺一尺向前靠;人退进了树林,大鱼却靠了岸。突然,一个鲤鱼打挺,眼前金光一闪,线断了……
回来向钓友汇报,大伙儿拿他开涮:“咱老孙真猛,只认焖竿,不认回线;鱼上岸不管,他进树林儿了。”事隔多年,孙哥一讲起那次遭遇战,仍旧懊恼不已。他说,那大鱼跑的能让他后悔一辈子,当时的心情就别提了,连撒尿都是黄的。
三、哥们组合
机关里酷爱垂钓的越来越多。不过要论对脾气的,够“铁的”,还得属张、王、李和我,俗称“四人帮”。冬天来了,千里冰封,苦闷的很,闲暇时哥四个总要凑到一起,谈谈钓组,化化铅坠儿,研发“地崩子”什么的。星期天更难熬,拎出竿包,开始“擦枪”;擦完了,还忍不住伸展枪身,在屋里操练。就连除夕接神燃爆竹,都得用鱼竿挑着放。春天总算来了,我们从此披星戴月,南征北战,不知道啥叫礼拜天。孩儿他娘时常提醒:“你们都是坐机关的,注意点儿形象,脸儿晒得象非洲来的。”
李哥是我们四人中的老大,底板黑,人晒得更黑,冷眼一瞧整个儿一肯尼亚的。据说他上小学时头发就花白,等我们认识的时候已经是“洪七公”了。因此哥三个习惯叫他老李头儿。老李头儿人实诚,写一手好字,毛病就是不爱主动说话。跟他对面坐,你要不出声,他能焖一天;你要出声,尤其是谈钓鱼,他能跟你唠一天。
如果说桃园三结是最佳组合、西天取经是优秀组合,我们四个可算得上真正的哥们组合。不过,再好的夫妻也免不了吵架,再好的哥们儿也有怄气的时候。
一个夏日的周末,我提议明天去黄金水库,时间定在次日凌晨两点半,爱心医院前不见不散,用范伟的话叫“妥妥地”。结果,我一觉醒来已经接近五点,天都大亮了。原以为那哥仨儿都去了,而最终一落实:除了老李头儿,谁都没去。并听说老李头儿因攀砬头儿手受了伤,还滚到湖里,差点儿没出人命。“真不好意思。”
星期一上班,在三楼与李哥狭路相逢。他扭着头没理我,悻悻地,左手裹了绷带。我想主动上前解释,可没等我开口,他却瓮声瓮气边走边喊:“损哪!都他们定的,他们他妈不去。损哪!”
四、青出于蓝
五养厂有一对师徒,天一热总习惯留光头,于是单位的人常叫他们“师徒和尚”。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场里,小和尚言听计从没的说;在水边垂钓,还是师父领上的道儿。在他的心中,师父就是湖,深不可测。
小和尚第二次随师父出征,已是金色的秋天,地点选定在丁家水库。那水库建库快二十年了,听说历史上登陆的鲤鱼大的有三十来斤。太阳攀上山头,层林尽染,宁静的水面折射出七彩的倒影。师父开始上鱼了,一条接一条,几乎竿竿不空。而小和尚手忙脚乱,连钩还没下水。好歹把竿投出去,可漂却忘了插。师父转头瞅瞅,撂下竿过去帮忙。漂调好了,他对徒弟讲:“这食儿上得太大,‘迁西板栗’似的,你当是喂猪!”小和尚终于下竿了,接着便是东一头、西一下,一会儿挂手,一会儿与师父搭钩。大和尚实在忍不住了,说:“我看你现在没个准星,去找宽敞地方练吧。最好离我远点儿。”小和尚不高兴了,心想:“远就远点儿。手竿儿我还不钓了,抛竿行不?”于是他移开师父两丈多远,抡起了海竿。
太阳渐渐偏西了,牧哥驱着羊群顺山路开始回家,间或传来“米啊”的叫声。师父的鱼护装了半截,徒弟则舞枪弄棒,没见收获。只见他竿也断了,手牵着主线,上扯下拽,累得满头是汗。师父问:“有鱼吗?”他回答:“不知道。”
又过了许久,小和尚突然大叫起来:“啊!难产!是难产!”师父闻声奔到近前,定神儿一看,傻眼了:三把钩挂在尾巴上,十多斤的大草鱼被徒弟倒着扯上了岸。
“神了!”
五、修成正果
时下,“各村的地道都有许多高招儿”,各行当都有登峰造极的。搓麻的几宿不睡,喝酒的斤八不醉,跳舞的啥步都会,念经的得书就背。想了半天,钓鱼人怎样才算“上梃”、修成正果了呢?还是女儿有学问,念大学的就比我强,她从网上发来邮件,对钓翁的最高境界做了描述。诗云:
日落西山红霞飞,方得三更人未睡。
大鱼小鱼不开口,笑傲空囊把家回。
想起来,从小就跟鱼交手,可真正加入垂钓大军还是近十年的事。起初,妻女随我去钓鱼,总是添乱。要么往水里扔石头,要么嚷着吃“盒儿饭”。等盒饭吃完了,呆得闹心,太阳老高就吵着回家。气得我把鱼竿都踹了,发誓“下辈子不钓了!”而钓鱼人很像抽烟人,常常喊“戒”,可往往是当面不抽,背后乱抽;或人前小抽,没人大抽。即便暂时戒了,一旦捡起来,抽得更凶。竿踹了,没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否定之否定嘛。原来玻璃钢的换成碳素的,三米六的增到五米四的。步步升级?怎的,就没脸,气死你!
不过日子一长,总拉硬儿也不是办法,家和鱼才兴。何况咱毕竟是家庭的民族领袖,“曲线救国”方为上策。
记得在腰堡水库垂钓,我那次一改常态,很民主地发给妻子一把小手竿,并手把手做辅导,循循善诱。结果一天下来,妻子居然钓了五、六十条,大的有一斤多重。第二天起床,妻对我说:昨夜睡的不好,一闭眼那鱼漂老在眼前晃。我心想:“好,这就快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精心栽培,娘俩终于让我带上了“革命道路”,钓技上基本到达专科水平。现在每逢五一、十一长假,我问怎么安排,娘俩会异口同声说“钓鱼”。出征的头天晚上,真是开心。妻子准备人吃的,姑娘准备鱼吃的,还要整理钓具、帽子、眼镜。
问我做啥?老外了不是。我那时手一背,喊“沏水!”然后手握遥控器,看“四海钓鱼”。(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