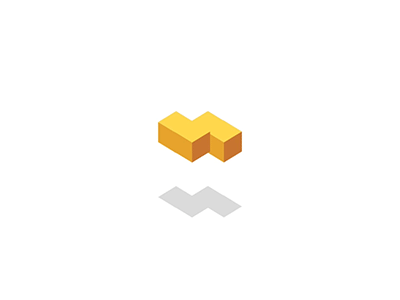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
 “几年前我常去莫尔道河上的西冷特伦克,在那儿逆水划船,然后伸展四肢平躺在船上,顺流而下,从桥下穿过。因为我很瘦,从桥上看一定很可笑。那个职员有一次从桥上看见了我,在充分强调了我的可笑样子后,可把他的印象归结为:我看上去就像是在最后的审判时刻那样。这或许可以说像棺材盖已打开,而所有死人仍躺着不动的那个时刻。”
“几年前我常去莫尔道河上的西冷特伦克,在那儿逆水划船,然后伸展四肢平躺在船上,顺流而下,从桥下穿过。因为我很瘦,从桥上看一定很可笑。那个职员有一次从桥上看见了我,在充分强调了我的可笑样子后,可把他的印象归结为:我看上去就像是在最后的审判时刻那样。这或许可以说像棺材盖已打开,而所有死人仍躺着不动的那个时刻。”
“这主意简要来说就是:您离开您的丈夫一段时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已经有过一次先例了。理由是:您的病,他的神经质(您这么做也能使他轻松一下),再就是维也纳的状况。我不知道您要到哪里去,最好能到波希米亚任何一个安宁的所在。要是我自己不插手,也不表态,那是再好不过的了。需要的钱您暂时从我这里拿(关于怎么偿还我们还可以商量。我为此只提一个也许我能从中得到的次要好处:我将成为一个热衷于工作的职员——话说回来,我的工作轻松得可笑又可卑,这您也许无法想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赚到钱)。假如每个月这笔钱有时不太够,所缺的零头您总有办法轻而易举地解决的。”
“真是愚蠢的典范,我正在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读到对西藏边境山中一个村落的描写时,我的心突然痛楚起来。这村落在那里显得那么孤零零,几乎与世隔绝,离维也纳那么遥远。说西藏离维也纳很远,这种想法我称之为愚蠢。难道它真的很远吗?”
“您不要求我正直,密伦娜,除了我自己之外,谁也不能再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了,很多东西正从我身上消失呢,一点不假,也许一切都正在从我身上消失,但是这在狩猎场上鼓舞士气却鼓舞不了我的心。正相反,我会因此而迈不动步子。突然间一切都会变成骗局,被猎者会把猎人掐死。我就是走在一条如此危险的道路上,密伦娜。您站在一棵树旁一动不动,年轻、漂亮,您的眼睛把这世界的苦难反射到地上。人们在玩‘小树、小树、换换个,小树’的游戏,我在阴影下从一棵树下潜行到另一棵树下。我正走在半路上,您向我呼叫,叫我当心危险,想给我以勇气,对我不稳的脚步感到惊恐,提醒我!不要忘了这是游戏——但我不能,我倒下了,我已经躺下了。我不能同时倾听内心可怕的声音和您的声音,但我能听见那个声音并信赖您,您,除此之外在这个世界上我谁都不能信赖了。”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密伦娜,我们是那么的怯懦,每封信几乎都面目全非,几乎每一封信都对上一封信或下一封回信感到惊恐。很容易看出,这不是出自您的天性,甚至可能不是出自我的天性,但几乎化成了我们的天性。但这种怯懦只有在绝望中、顶多在愤怒中,噢,不要忘了,还有:在恐惧中才会消逝。”
“有时候我有这么个印象:我们有个房间,这房间有两个互相对着的门,我们每人攥着一扇门的把手,只要一个人的睫毛动一下,另一个就站到这个人的门后了;只要第一个人说一句话,第二个就带上了身后的门,并且再也看不见了。当然他也许会重新打开这扇门,因为这是一个也许离开不了的房间。只要第一个人不完全像第二个一样,他就会很安静,他表面上仿佛根本不朝第二个人看一眼。他会慢慢地整理房间,好像这房间和其他任何房间一样似的。尽管这样,他总要在他那门旁重复同样的动作,有时两个人甚至同时跑到门外,于是这美丽的房间便空无一人了。”

“这主意简要来说就是:您离开您的丈夫一段时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已经有过一次先例了。理由是:您的病,他的神经质(您这么做也能使他轻松一下),再就是维也纳的状况。我不知道您要到哪里去,最好能到波希米亚任何一个安宁的所在。要是我自己不插手,也不表态,那是再好不过的了。需要的钱您暂时从我这里拿(关于怎么偿还我们还可以商量。我为此只提一个也许我能从中得到的次要好处:我将成为一个热衷于工作的职员——话说回来,我的工作轻松得可笑又可卑,这您也许无法想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赚到钱)。假如每个月这笔钱有时不太够,所缺的零头您总有办法轻而易举地解决的。”
“真是愚蠢的典范,我正在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读到对西藏边境山中一个村落的描写时,我的心突然痛楚起来。这村落在那里显得那么孤零零,几乎与世隔绝,离维也纳那么遥远。说西藏离维也纳很远,这种想法我称之为愚蠢。难道它真的很远吗?”
“您不要求我正直,密伦娜,除了我自己之外,谁也不能再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了,很多东西正从我身上消失呢,一点不假,也许一切都正在从我身上消失,但是这在狩猎场上鼓舞士气却鼓舞不了我的心。正相反,我会因此而迈不动步子。突然间一切都会变成骗局,被猎者会把猎人掐死。我就是走在一条如此危险的道路上,密伦娜。您站在一棵树旁一动不动,年轻、漂亮,您的眼睛把这世界的苦难反射到地上。人们在玩‘小树、小树、换换个,小树’的游戏,我在阴影下从一棵树下潜行到另一棵树下。我正走在半路上,您向我呼叫,叫我当心危险,想给我以勇气,对我不稳的脚步感到惊恐,提醒我!不要忘了这是游戏——但我不能,我倒下了,我已经躺下了。我不能同时倾听内心可怕的声音和您的声音,但我能听见那个声音并信赖您,您,除此之外在这个世界上我谁都不能信赖了。”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密伦娜,我们是那么的怯懦,每封信几乎都面目全非,几乎每一封信都对上一封信或下一封回信感到惊恐。很容易看出,这不是出自您的天性,甚至可能不是出自我的天性,但几乎化成了我们的天性。但这种怯懦只有在绝望中、顶多在愤怒中,噢,不要忘了,还有:在恐惧中才会消逝。”
“有时候我有这么个印象:我们有个房间,这房间有两个互相对着的门,我们每人攥着一扇门的把手,只要一个人的睫毛动一下,另一个就站到这个人的门后了;只要第一个人说一句话,第二个就带上了身后的门,并且再也看不见了。当然他也许会重新打开这扇门,因为这是一个也许离开不了的房间。只要第一个人不完全像第二个一样,他就会很安静,他表面上仿佛根本不朝第二个人看一眼。他会慢慢地整理房间,好像这房间和其他任何房间一样似的。尽管这样,他总要在他那门旁重复同样的动作,有时两个人甚至同时跑到门外,于是这美丽的房间便空无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