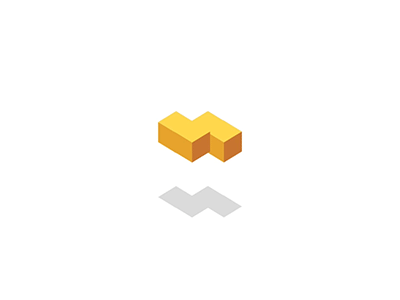我曾认识一个有名的射手,名叫威廉·伊文。他是菲拉特尔非亚的律师,但他打官司远不及打枪出名。我们曾一同打猎多日,倒是一对好搭档:我有好猎犬,对人家说我枪法好坏毫不介意;他的猎犬一无用处,但他珍惜射手的令名则远远超过律师的声誉。我要在下面叙述一件关于他的事情,它应该成为对年轻人的忠告,叫他们注意不要染上这类的虚荣恶习。
我们结伴到离家约十哩处去打猎,听说那里鹧鸪很多,到了一看,果然如此。时间是十一月,打了一天,到天黑之前,他打的鹧鸪,连送回家的和装在袋子里的,总共九十九只。有几枪他是一箭双雕,但也可能有几枪没有打中,因为隔着树林,有一阵我没有亲眼看见他。不过他说他是百发百中。等我们在农舍吃了晚饭,他擦过了枪,点了点鹧鸪的数目,知道这一天在日落之前,他打下了九十九只,每只都打在了翅膀上,多数是在有很多大树的密林中打的。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可是,不幸得很,他要凑成一百只的数目。太阳已经落山了,那地方说黑就黑,象蜡烛突然熄灭,而不是象火炉慢慢消失。我想赶紧回家,因为路不好走,而他这位素来怕老婆的人又早已得到闺中的严令,叫他当夜必须赶回,由于马车是我的,还必须与我同行。因此我劝他快走,并向农舍走去(房子在布克思郡,是约翰.布朗老人的,老人是布朗将军的祖父,将军曾在上次那场“为了逼詹姆士.麦迪逊退位”的战争里给了我们的胡子兵一个迎头痛击);本来我可以就在那里过夜,可是由于他三生有幸,都在太太的严厉管束下过活,连我也不得不离开了。因此,我就急于上路。可是不!他一定要打下第一百只鹧鸪。我说路不好走,又没有月亮,有种种危险,但他根本不听。被我们惊散了的可怜的鹧鸪正在四周叫唤着;突然之间,有一只从他脚下飞起,当时他正站在有三四吋高的麦苗的田里,立即开枪,可是没有打中。“好了,”他边说边跑,象是要去拾起那只鹧鸪似的。“什么!”我说,“你该不是说你打中了吧?那鹧鸪不但没有死,还在叫呐,就在那树林里!”树林离我们约一百码。他用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一类话,一口咬定说他打中了,而且还是亲眼看见鹧鸪落地的;我呢,也用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的一类话,一口咬定说他没打中,而且还是我亲眼看见那鹧鸪飞进树林的。一百次里失手一次,这可太严重了!难道就丢掉这样一个名垂不朽的大好机会?他平时是一个和善的人,我也很喜欢他。这时他说:“老兄,我确是打中了,如果你定要走开,而且连狗也要带走,叫我没法找到这只鹧鸪,那么请便吧,狗当然是你的。”这话叫我替他难受,我就用十分温和的口气对他说:“别提狗了——伊文兄,刚才那只鹧鸪是从那边地上起飞的。要是它真的落了地,这样一片平整光滑的绿草地上还能看不见吗?”我说我的,可他已在寻找了。我只叫了狗来,也装着帮他寻找。这时我已不在乎走夜路的危险,倒是可怜起这个人的毛病来了。在不到二十码的地上,我们两人眼睛看着地,走了许多来回,寻找着我们彼此都完全明白是根本没有的东西。我们各从一边起始,到中间交叉而过,有一次我走过他之后,恰好回头一看,这一看不打紧,只见他伸手从背后的袋里拿出一只鹧鸪,扔在地上。我不愿戳穿他,赶紧回头,仍旧装着到处寻找的样子。果然,他一回到刚才扔鹧鸪的地方,就用异常得意的声调向我大叫:“这儿!这儿!快来!”等我走上去,他就用手指点着鹧鸪,同时眼睛紧盯着我,口里说:“你瞧,科贝特!我希望这是对你的忠告,以后万万不要再任性了!”我说:“好,走吧。”这样我们两人就兴高采烈地走了。到了勃朗家里,他把这件公案告诉了他们,得意洋洋地大声拿我取笑。以后他也常常当我的面说起此事。我一直不忍心让他知道:我完全明白一个通情达理的高尚的人怎样在可笑的虚荣心的勾引下,干了骗人的下流事情。
——[英]威廉·科贝特:《骑马乡行记.射手》
威廉.科贝特的《射手》通过打猎事件,把名射手威廉.伊文的虚荣心暴露无遗。作者对事件的叙述,凝聚为一个横断面。详细而不混杂,具体而不烦琐。并注意通过对比,表现人物的性格和主题。
我曾认识一个有名的射手,名叫威廉·伊文。他是菲拉特尔非亚的律师,但他打官司远不及打枪出名。我们曾一同打猎多日,倒是一对好搭档:我有好猎犬,对人家说我枪法好坏毫不介意;他的猎犬一无用处,但他珍惜射手的令名则远远超过律师的声誉。我要在下面叙述一件关于他的事情,它应该成为对年轻人的忠告,叫他们注意不要染上这类的虚荣恶习。
我们结伴到离家约十哩处去打猎,听说那里鹧鸪很多,到了一看,果然如此。时间是十一月,打了一天,到天黑之前,他打的鹧鸪,连送回家的和装在袋子里的,总共九十九只。有几枪他是一箭双雕,但也可能有几枪没有打中,因为隔着树林,有一阵我没有亲眼看见他。不过他说他是百发百中。等我们在农舍吃了晚饭,他擦过了枪,点了点鹧鸪的数目,知道这一天在日落之前,他打下了九十九只,每只都打在了翅膀上,多数是在有很多大树的密林中打的。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可是,不幸得很,他要凑成一百只的数目。太阳已经落山了,那地方说黑就黑,象蜡烛突然熄灭,而不是象火炉慢慢消失。我想赶紧回家,因为路不好走,而他这位素来怕老婆的人又早已得到闺中的严令,叫他当夜必须赶回,由于马车是我的,还必须与我同行。因此我劝他快走,并向农舍走去(房子在布克思郡,是约翰.布朗老人的,老人是布朗将军的祖父,将军曾在上次那场“为了逼詹姆士.麦迪逊退位”的战争里给了我们的胡子兵一个迎头痛击);本来我可以就在那里过夜,可是由于他三生有幸,都在太太的严厉管束下过活,连我也不得不离开了。因此,我就急于上路。可是不!他一定要打下第一百只鹧鸪。我说路不好走,又没有月亮,有种种危险,但他根本不听。被我们惊散了的可怜的鹧鸪正在四周叫唤着;突然之间,有一只从他脚下飞起,当时他正站在有三四吋高的麦苗的田里,立即开枪,可是没有打中。“好了,”他边说边跑,象是要去拾起那只鹧鸪似的。“什么!”我说,“你该不是说你打中了吧?那鹧鸪不但没有死,还在叫呐,就在那树林里!”树林离我们约一百码。他用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一类话,一口咬定说他打中了,而且还是亲眼看见鹧鸪落地的;我呢,也用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的一类话,一口咬定说他没打中,而且还是我亲眼看见那鹧鸪飞进树林的。一百次里失手一次,这可太严重了!难道就丢掉这样一个名垂不朽的大好机会?他平时是一个和善的人,我也很喜欢他。这时他说:“老兄,我确是打中了,如果你定要走开,而且连狗也要带走,叫我没法找到这只鹧鸪,那么请便吧,狗当然是你的。”这话叫我替他难受,我就用十分温和的口气对他说:“别提狗了——伊文兄,刚才那只鹧鸪是从那边地上起飞的。要是它真的落了地,这样一片平整光滑的绿草地上还能看不见吗?”我说我的,可他已在寻找了。我只叫了狗来,也装着帮他寻找。这时我已不在乎走夜路的危险,倒是可怜起这个人的毛病来了。在不到二十码的地上,我们两人眼睛看着地,走了许多来回,寻找着我们彼此都完全明白是根本没有的东西。我们各从一边起始,到中间交叉而过,有一次我走过他之后,恰好回头一看,这一看不打紧,只见他伸手从背后的袋里拿出一只鹧鸪,扔在地上。我不愿戳穿他,赶紧回头,仍旧装着到处寻找的样子。果然,他一回到刚才扔鹧鸪的地方,就用异常得意的声调向我大叫:“这儿!这儿!快来!”等我走上去,他就用手指点着鹧鸪,同时眼睛紧盯着我,口里说:“你瞧,科贝特!我希望这是对你的忠告,以后万万不要再任性了!”我说:“好,走吧。”这样我们两人就兴高采烈地走了。到了勃朗家里,他把这件公案告诉了他们,得意洋洋地大声拿我取笑。以后他也常常当我的面说起此事。我一直不忍心让他知道:我完全明白一个通情达理的高尚的人怎样在可笑的虚荣心的勾引下,干了骗人的下流事情。
——[英]威廉·科贝特:《骑马乡行记.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