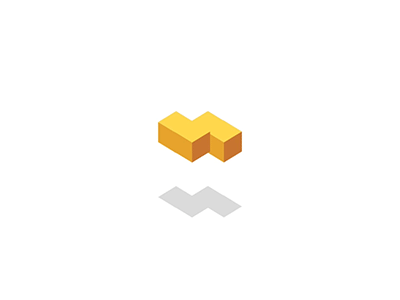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

篇一:那个冬天不冷
眺望那遥远的天际,找不到尽头,就如我心中的忧伤绵绵无尽,即使到我死去那一刻,忧愁也依然会如影随形般吞噬我的灵魂……我知道一切都将离我而去,一切都将我抛弃。曾经的岁月,像从旧书里掉出的发黄的花一瓣,无声地掉落在我的手心,然后随风飘散。我只能躲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一舔一舐一着自己的伤口。泪,已干涸;痛,已麻木。我仓惶逃离那座城市,逃离那段婚姻留下的伤痛,来到北方的一座城市,将所有的痛让冰雪冻结在那个冬天里。
我想,我首先得找个工作,租好房子。然而,没有想到,要想在这个城市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真的很难。我不知道递了多少份个人资料,跑了多少家公司,始终未能如愿.四处碰壁。难道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真的就没有我的一席之地吗?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这个季节遗弃.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座城市的冬天会那么冷,我有时甚至想我能熬过这个萧瑟的季节吗?
那天,天气-阴-沉,满天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西北风呜呜地吼叫,肆虐地在旷野里奔跑,它仿佛握着锐利的刀剑,能刺穿严严实实的皮袄,更别说那暴露在外面的脸皮,被它划了一刀又一刀,疼痛难熬。令我想起孟郊的《苦寒吟》“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这样的天气,我只能又强打起精神,准备到一家广告公司去碰碰运气。走在半路上,也许是感情的痛楚,求职的艰辛,冬日的凄寒,我突然感到全身乏力、头痛、恶心,特别是右下腹疼痛难忍,我双手捂住肚子,无助地蹲了下去。
“怎么了?”一个浑厚的男中音,透着关切,“痛……”我非常吃力地说。“我送你去看医生,好吗”我艰难地点了点头。他扶着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将我送到医院,陪着我挂号,检查。医生初步怀疑是急性*阑尾炎。在经过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等一系列的检查确定了急性*阑尾炎,并且需要马上做手术。
“你的家人呢?我帮你打电话通知他们。”我无力地摇了摇头:“我就一个人。”泪水立即涌了出来:“谢谢你,没有多大关系,过几天我再来做手术。”我硬撑着,想离开医院。当初离开那个家时身上的钱都用得差不多了。我想,生既然这样难,也许解脱了更好。
他可能看出了一些,轻轻地说道:“必须马上做,如果是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他不等我发表任何意见,接着说:“你等我打个电话,不要走开。”
只有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我老婆马上就会来了,我们一会就去办住院手续。”此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任泪水恣意地流淌。我几乎不相信,在这个凄寒的冬天,我会遇到这么好的人。
没多久,他的老婆来了,我被两位素不相识的人送进手术室。在手术台上,我迷迷糊糊,似乎一切都在梦境中,我仿佛已经走过漫长的冬日,温情的春正张开双臂拥抱我,我似乎已经闻到春花的芬芳,泥土的气息。
手术非常成功,那对善良的夫妻将我送到病房,躺在病床上,望着两位陌生而亲切的面孔,我居然现在才看清楚他们的样子。男的叫曾鹏飞,在一家公司当经理,女的叫柳红,是一名教师。我几次想说什么但是都不知该从何说起。“妹一子,什么也不用说,好好养病,出门在外,谁不遇到点难处,你还年轻,慢慢来,啊。”红姐一边说,一边帮我擦去腮边的泪水。“我以后有了钱一定马上还给你们的。”老半天,我就想出这么一句没有水准的话。“不要着急,你就把我们当成你的哥哥嫂嫂,我们以后就是你的亲人。”鹏飞哥说道。一种久违了的亲情袭来,我居然有些不适应。一种与这个季节不相适应的暖流涌一入我的身心。
在医院的日子里,这对与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夫妻每天都要来看我,抚一慰我。在他们悉心照顾下,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后来,红姐还介绍我到她的一位好朋友的公司上班。工作很轻松,待遇也不错。
真的感到,命运还是很公平的,让我经历了一次巨大的伤痛后,再让我感受如此温情。是的,我应该感谢命运,让我领略到难得的人间真情。我应该感谢那个不冷的冬天,让我领略到生命的美好!
篇二:那个冬天好冷
北疆的冬天,似乎比别处都寒冷:气温总是在零下十多二十几度,我和你就完全困在那间土屋里了。虽然屋里也燃起了火炉,但烧的都是柴火,火力无法抵御严寒入侵,所以房间总是给人很冷的感觉。望着炉里那无力的火焰,有时候我会发神经地踢上一脚;看着那火焰熬着半锅面粉糊糊,咕咚咕咚乱叫,我心里就很烦躁,把端在手里等着舀糊糊的碗摔碎。你在一旁总是不吭声,搓着那双布满老茧的宽厚的手掌,看着我又钻进被窝去暖和身子的时候,你会把我踢歪的火炉扶正,把我摔碎的碗片扫在一旁,同时用你的碗把煮熟的面糊糊给我端过来。你总是这样默默无声的承受一切。有时候你会安慰我:“再忍几天,我们把工钱拿回来就好过了。“我没好气地对你叫道:“拿个屁!那工头卷着钱跑得都没影了。”
我大声地叫嚷,好像是你的错:“等着吧,我们只能在这儿冻死饿死!”你木讷地站在一旁低语:“不会的,工头的家就住在这里 … …”我知道,你总是隔三岔五冒着严寒,到工头家去要钱,可你并没见着工头。后来有老乡告诉我,你到工头家去,常被他家人赶出来,并挨他们的耳光。(中国- sanwen.aiisen.com)
我们是春天刚解冻的时候,就跟着工头干活的。由于我腿有残疾,你总是帮助我,是重活都是你抢去干了。从你我说话的口音里听得出来,我们并不是老乡:你是河南驻马店人,而我却是四川西充人。虽然我们口音不一样,有时还听不懂对方的方言,生活习惯也并不一样,可这些并没影响我们交往,成为好朋友。你总是那么憨厚实在,有人说:“小陈,那稀饭剩着浪费了,你把它吃了哈。”你说:“我来我来。”那小半盆稀饭又被你装进肚里。有人说:“小陈,抬板。”你说:“我来我来。”就听到那“嗨哟嗨哟”哼着的号子,你和大家一起,把沉重的水泥板抬到墙顶。只到霜降封冻,大雪已经覆盖了工地的时候,我们才停止了干活,就等着工头结帐回家过年。可不曾想到,工头却卷着钱躲开了,让我们十几个干活的民工都没拿上钱。好在你平时为人忠厚,认识你的人都知道你,就帮忙找了一间土屋让住下来。大概是长期没人住的原故,土屋的墙壁总是大块大块剥落泥土,到处都是通风口,这在新疆这样寒冷的冬天来说,是根本无法住人的。你就找来木板和塑料纸把通风口堵了,找来火炉,去别处的棉地里,背回来大捆大捆的棉花杆,我和你就在那地方住下了。
我知道,就连这样的日子,我们也坚持不了多久。你我身上,总共还没有20元钱;这吃的面粉,眼看就快完了。我感到忧虑和慌乱起来,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容易发脾气。
那天我坐在被窝里,忐忑不安地想着这快无法过下去的日子,正在唉声叹气的时候,你从外面回来,走到床跟前对我说:“我去了工头家,可还是没见着人。”
“哪怎么办呢?”我无力地问,好像你是我唯一的救星,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谁知道呢。”你却摇摇头,就见你那紊乱的头发在我眼前幌动,你那从不撒谎的眼睛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再想想法……”你说。
“是呀,要不这冬天我们没法过了。”我说。你那年轻的褐色的。却横着两沟皱纹的额头便点了几下,用你那宽厚粗糙的手掌摸着自己胡子八楂的下巴沉思着说:“得去老乡家,看能不能借点钱。”我虽然在新疆也有好几年了,可平时挣不上什么钱,别人一般是不同我打交道的,更不用说去借什么钱了。这借钱的事,还真要你出面解决。可你却又犯难了,坐在床边不停地抓着头皮说:“老王已经回山东过年去了,狗子去了乌鲁木齐,那小杨搬到他姐姐家去了,虽然不远,可不知具体地址。。。。。对了,到他那儿看看……”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大概是和你关系要好的人。直到快天黑,你回来了,手里拧着半袋面粉,脸色被严寒冻得发紫,你搓着手吹着,坐在火炉旁还咻咻地吸着干裂的嘴唇,一手不停地捂左右两只耳朵,一手把棉花杆放进炉里……
我坐在床上的被窝里默默地看着你,不用问,我就知道你没借上钱。过了一会,你大概是暖和了身子,有了说话的力气,站起身来面对我说:“这钱不好借,好不容易借回半袋面粉。。。。”。你走过来,“不过,我听说那工头回来了,我得到他家去看看……”
你到外面去提了两桶水回来,对我说:“天冷,你早点做饭吃,我去看看。”
我说:“你吃了晚饭再去吧。”
“不用,”你说,“我刚才在老乡家吃过饭了。”
你就转身走近门跟前,正准备推门出去,却忽然停住了,又回过身来,走到我前面,从你那陈旧破口的棉衣口袋里,捣出一个纸团来,放在鼻下闻了闻后交给我:“这是刚才我在老乡家吃饭,偷偷给你包的几片肉……”
你出去了,可再没有回来。
警察来抓你的时候,那雪地里到处都是血,那把砍工头的菜刀,就掉在你脚旁的雪地里。我没想到你和工头发生了冲突,会拿他家的菜刀砍他。看着你被警车带走,认识你的人都摇头叹息。
我无比难过,就到派出所去看你,可是不管我怎么说,人家就是不让我见你。
那个冬天真的好冷,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在寒风的怒吼下,苍白得让人惨然!只到第二年的秋天,我才知道你被判了七年徒刑,送到了南疆的和田去服刑了。我总是想去看你,可我总是凑不够往返的车旅费啊。我就计算着你出监的时间,七个寒冬过去了,到了你该归来的日子,可是你没有回来,不知你去了什么地方。
如今,我在温暖的南方,但是一到冬天,我依旧感到寒气袭人,因为我的心,总在那片茫茫雪地里,等你归来的脚步声。
但是那个冬天好冷,一切都被时间冻结;迄今,还没解冻……

篇一:那个冬天不冷
眺望那遥远的天际,找不到尽头,就如我心中的忧伤绵绵无尽,即使到我死去那一刻,忧愁也依然会如影随形般吞噬我的灵魂……我知道一切都将离我而去,一切都将我抛弃。曾经的岁月,像从旧书里掉出的发黄的花一瓣,无声地掉落在我的手心,然后随风飘散。我只能躲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一舔一舐一着自己的伤口。泪,已干涸;痛,已麻木。我仓惶逃离那座城市,逃离那段婚姻留下的伤痛,来到北方的一座城市,将所有的痛让冰雪冻结在那个冬天里。
我想,我首先得找个工作,租好房子。然而,没有想到,要想在这个城市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真的很难。我不知道递了多少份个人资料,跑了多少家公司,始终未能如愿.四处碰壁。难道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真的就没有我的一席之地吗?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这个季节遗弃.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座城市的冬天会那么冷,我有时甚至想我能熬过这个萧瑟的季节吗?
那天,天气-阴-沉,满天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西北风呜呜地吼叫,肆虐地在旷野里奔跑,它仿佛握着锐利的刀剑,能刺穿严严实实的皮袄,更别说那暴露在外面的脸皮,被它划了一刀又一刀,疼痛难熬。令我想起孟郊的《苦寒吟》“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这样的天气,我只能又强打起精神,准备到一家广告公司去碰碰运气。走在半路上,也许是感情的痛楚,求职的艰辛,冬日的凄寒,我突然感到全身乏力、头痛、恶心,特别是右下腹疼痛难忍,我双手捂住肚子,无助地蹲了下去。
“怎么了?”一个浑厚的男中音,透着关切,“痛……”我非常吃力地说。“我送你去看医生,好吗”我艰难地点了点头。他扶着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将我送到医院,陪着我挂号,检查。医生初步怀疑是急性*阑尾炎。在经过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等一系列的检查确定了急性*阑尾炎,并且需要马上做手术。
“你的家人呢?我帮你打电话通知他们。”我无力地摇了摇头:“我就一个人。”泪水立即涌了出来:“谢谢你,没有多大关系,过几天我再来做手术。”我硬撑着,想离开医院。当初离开那个家时身上的钱都用得差不多了。我想,生既然这样难,也许解脱了更好。
他可能看出了一些,轻轻地说道:“必须马上做,如果是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他不等我发表任何意见,接着说:“你等我打个电话,不要走开。”
只有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我老婆马上就会来了,我们一会就去办住院手续。”此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任泪水恣意地流淌。我几乎不相信,在这个凄寒的冬天,我会遇到这么好的人。
没多久,他的老婆来了,我被两位素不相识的人送进手术室。在手术台上,我迷迷糊糊,似乎一切都在梦境中,我仿佛已经走过漫长的冬日,温情的春正张开双臂拥抱我,我似乎已经闻到春花的芬芳,泥土的气息。
手术非常成功,那对善良的夫妻将我送到病房,躺在病床上,望着两位陌生而亲切的面孔,我居然现在才看清楚他们的样子。男的叫曾鹏飞,在一家公司当经理,女的叫柳红,是一名教师。我几次想说什么但是都不知该从何说起。“妹一子,什么也不用说,好好养病,出门在外,谁不遇到点难处,你还年轻,慢慢来,啊。”红姐一边说,一边帮我擦去腮边的泪水。“我以后有了钱一定马上还给你们的。”老半天,我就想出这么一句没有水准的话。“不要着急,你就把我们当成你的哥哥嫂嫂,我们以后就是你的亲人。”鹏飞哥说道。一种久违了的亲情袭来,我居然有些不适应。一种与这个季节不相适应的暖流涌一入我的身心。
在医院的日子里,这对与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夫妻每天都要来看我,抚一慰我。在他们悉心照顾下,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后来,红姐还介绍我到她的一位好朋友的公司上班。工作很轻松,待遇也不错。
真的感到,命运还是很公平的,让我经历了一次巨大的伤痛后,再让我感受如此温情。是的,我应该感谢命运,让我领略到难得的人间真情。我应该感谢那个不冷的冬天,让我领略到生命的美好!
篇二:那个冬天好冷
北疆的冬天,似乎比别处都寒冷:气温总是在零下十多二十几度,我和你就完全困在那间土屋里了。虽然屋里也燃起了火炉,但烧的都是柴火,火力无法抵御严寒入侵,所以房间总是给人很冷的感觉。望着炉里那无力的火焰,有时候我会发神经地踢上一脚;看着那火焰熬着半锅面粉糊糊,咕咚咕咚乱叫,我心里就很烦躁,把端在手里等着舀糊糊的碗摔碎。你在一旁总是不吭声,搓着那双布满老茧的宽厚的手掌,看着我又钻进被窝去暖和身子的时候,你会把我踢歪的火炉扶正,把我摔碎的碗片扫在一旁,同时用你的碗把煮熟的面糊糊给我端过来。你总是这样默默无声的承受一切。有时候你会安慰我:“再忍几天,我们把工钱拿回来就好过了。“我没好气地对你叫道:“拿个屁!那工头卷着钱跑得都没影了。”
我大声地叫嚷,好像是你的错:“等着吧,我们只能在这儿冻死饿死!”你木讷地站在一旁低语:“不会的,工头的家就住在这里 … …”我知道,你总是隔三岔五冒着严寒,到工头家去要钱,可你并没见着工头。后来有老乡告诉我,你到工头家去,常被他家人赶出来,并挨他们的耳光。(中国- sanwen.aiisen.com)
我们是春天刚解冻的时候,就跟着工头干活的。由于我腿有残疾,你总是帮助我,是重活都是你抢去干了。从你我说话的口音里听得出来,我们并不是老乡:你是河南驻马店人,而我却是四川西充人。虽然我们口音不一样,有时还听不懂对方的方言,生活习惯也并不一样,可这些并没影响我们交往,成为好朋友。你总是那么憨厚实在,有人说:“小陈,那稀饭剩着浪费了,你把它吃了哈。”你说:“我来我来。”那小半盆稀饭又被你装进肚里。有人说:“小陈,抬板。”你说:“我来我来。”就听到那“嗨哟嗨哟”哼着的号子,你和大家一起,把沉重的水泥板抬到墙顶。只到霜降封冻,大雪已经覆盖了工地的时候,我们才停止了干活,就等着工头结帐回家过年。可不曾想到,工头却卷着钱躲开了,让我们十几个干活的民工都没拿上钱。好在你平时为人忠厚,认识你的人都知道你,就帮忙找了一间土屋让住下来。大概是长期没人住的原故,土屋的墙壁总是大块大块剥落泥土,到处都是通风口,这在新疆这样寒冷的冬天来说,是根本无法住人的。你就找来木板和塑料纸把通风口堵了,找来火炉,去别处的棉地里,背回来大捆大捆的棉花杆,我和你就在那地方住下了。
我知道,就连这样的日子,我们也坚持不了多久。你我身上,总共还没有20元钱;这吃的面粉,眼看就快完了。我感到忧虑和慌乱起来,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容易发脾气。
那天我坐在被窝里,忐忑不安地想着这快无法过下去的日子,正在唉声叹气的时候,你从外面回来,走到床跟前对我说:“我去了工头家,可还是没见着人。”
“哪怎么办呢?”我无力地问,好像你是我唯一的救星,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谁知道呢。”你却摇摇头,就见你那紊乱的头发在我眼前幌动,你那从不撒谎的眼睛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再想想法……”你说。
“是呀,要不这冬天我们没法过了。”我说。你那年轻的褐色的。却横着两沟皱纹的额头便点了几下,用你那宽厚粗糙的手掌摸着自己胡子八楂的下巴沉思着说:“得去老乡家,看能不能借点钱。”我虽然在新疆也有好几年了,可平时挣不上什么钱,别人一般是不同我打交道的,更不用说去借什么钱了。这借钱的事,还真要你出面解决。可你却又犯难了,坐在床边不停地抓着头皮说:“老王已经回山东过年去了,狗子去了乌鲁木齐,那小杨搬到他姐姐家去了,虽然不远,可不知具体地址。。。。。对了,到他那儿看看……”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大概是和你关系要好的人。直到快天黑,你回来了,手里拧着半袋面粉,脸色被严寒冻得发紫,你搓着手吹着,坐在火炉旁还咻咻地吸着干裂的嘴唇,一手不停地捂左右两只耳朵,一手把棉花杆放进炉里……
我坐在床上的被窝里默默地看着你,不用问,我就知道你没借上钱。过了一会,你大概是暖和了身子,有了说话的力气,站起身来面对我说:“这钱不好借,好不容易借回半袋面粉。。。。”。你走过来,“不过,我听说那工头回来了,我得到他家去看看……”
你到外面去提了两桶水回来,对我说:“天冷,你早点做饭吃,我去看看。”
我说:“你吃了晚饭再去吧。”
“不用,”你说,“我刚才在老乡家吃过饭了。”
你就转身走近门跟前,正准备推门出去,却忽然停住了,又回过身来,走到我前面,从你那陈旧破口的棉衣口袋里,捣出一个纸团来,放在鼻下闻了闻后交给我:“这是刚才我在老乡家吃饭,偷偷给你包的几片肉……”
你出去了,可再没有回来。
警察来抓你的时候,那雪地里到处都是血,那把砍工头的菜刀,就掉在你脚旁的雪地里。我没想到你和工头发生了冲突,会拿他家的菜刀砍他。看着你被警车带走,认识你的人都摇头叹息。
我无比难过,就到派出所去看你,可是不管我怎么说,人家就是不让我见你。
那个冬天真的好冷,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在寒风的怒吼下,苍白得让人惨然!只到第二年的秋天,我才知道你被判了七年徒刑,送到了南疆的和田去服刑了。我总是想去看你,可我总是凑不够往返的车旅费啊。我就计算着你出监的时间,七个寒冬过去了,到了你该归来的日子,可是你没有回来,不知你去了什么地方。
如今,我在温暖的南方,但是一到冬天,我依旧感到寒气袭人,因为我的心,总在那片茫茫雪地里,等你归来的脚步声。
但是那个冬天好冷,一切都被时间冻结;迄今,还没解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