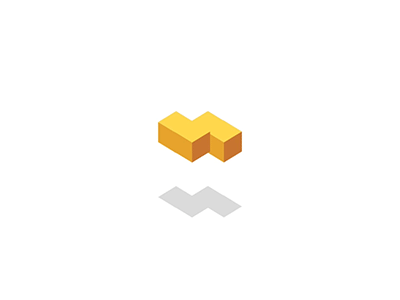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


从鹤城坐车到会峪沟向北约一个多小时,在会峪桥下车,左拐沿窨沟盘旋而上约三十分钟,一片松橡混交林怀抱着三间土瓦房,门前一合石磨,场边樱桃树上,黄鹂鸣叫不停的就是母亲的家。低矮的三间土房面朝蓝天下辽阔秋景。这是一处幽静偏僻的山坳,是神赐予我最神圣的去处。太阳每天准时照耀,牵牛花和蝴蝶常来常往。
就是这个偏僻小山坳,我在八十里之外想她了,就自然想到了那普照众生的一抹阳光,以及阳光下的土房与上苍施与土房的温暖与安静。
阳光从房山豁照到母亲睡的土炕上,母亲就侧楞着左胳膊强打精神坐起来,背靠山墙,期待静谧中的浅淡和沉寂。有人把门轻轻推开,是外甥女,她今天要为她的外婆,一位半身不遂缠身的74岁老人送饭。
一声外婆,外甥女就把一碗小米粥,递在了母亲的一只手上,看着母亲把稀饭一口一口吃完。吃馒头的时候,外甥女把馒头掰成小疙瘩,跪在母亲面前,把馍块喂在母亲嘴里。
临走时,母亲叮咛说,我娃过沟时小心,别栽跤。外甥女回答一声,外婆,你别担心,我都十岁了。
木门轻轻合上,母亲轻轻闭合眼睛,阳光走至她一头白发上,母亲仿佛一尊清静神安的菩萨。万籁俱寂中,孤独享用来自神灵给予她的一份宁静,三份安详。
房前面五十米宽的沟对面的一块高台上,是妹妹新起的五间砖房。宽敞,明亮。专门为母亲装修的小房里,沙发,茶几,电视、新床齐全,但母亲却愿意一直就住在她那土房中,风雨来去,她一住就是五六年。
母亲和父亲分开已有三十多年,三十多年的漫长牵挂,无论生活如何起伏,作为儿子,我都会在每一个节日去看望她,亲近她,安慰她。是无法忘却的血缘,让我尽不完的孝顺。每一次去一脸泪,返回一脸泪。大人的事儿女无法干预,但既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你身上有父母的血液在悄然流淌,悔恨和自责无济于事,只有默默为母亲做一些事情,尽一些孝顺,责无旁贷。
妹妹在电话里说,“妈说,让你买一包月饼,叫她尝尝。”
和那许多次一样,我站在门前场院上,先擦去眼泪,尽量做出高兴的样子把门轻轻推开。连衣睡着的母亲,就挪了一下在被子外的那只左胳膊。
我叫一声;“妈,是我,建刚,你儿子。”母亲就挣扎着往起坐,她很吃力,我就急忙上炕,右手搂着她,让她坐起来。
“我娃来了……”说着,母亲呜呜哭起来。“我娃来了。”
“妈,你儿子来了,你要高兴。”我搂着她说,“妈,你一流泪,我也要流泪。咱不流眼泪,啊?”
“妈,你先靠着墙,让我把鞋脱了?”
我努力地往后轻轻把她一拖,母亲便稳稳地靠在我怀里上。我说:“妈,你看,是不是你儿子?”母亲摸着我的脸,说:“是我娃,是我娃。”
在炕上,我把母亲搂在怀里。母亲有些不好意思,脸上又是笑,又是落泪。我给她擦着,擦着也就流泪了。但我尽量服从妹妹的安排,要把今天的气氛搞得高兴一些。
我说:“妈,今天我就陪你到下午最后一趟车再走。等会儿咱就吃月饼,吃水果?”母亲说:“我就是想你,就那么一说。你妹子就给你说了。你拿了一大包东西,又要花钱……”
母亲静静地看着我,抬起她那只左胳膊,在我脸上,抚摸着,擦着。“你哭啥,我娃不哭,咱娘儿俩都不哭?”但不一会儿,她又流眼泪。
我说:“妈,让我看你那胳膊?”
我抓起母亲的右胳膊,抓着它,就像拾起一根冰冷的木棍。我从手掌开始慢慢地往她肩膀处捋一会儿,再揉一会儿。
可母亲说她感觉不到,我说再捋一次,她就两眼泪水给我笑着:“我娃孝顺,可妈就是感觉不到啊。”我说:“妈,你感觉不到,我就多捋一会儿?”
这一次我把母亲的右胳膊,用一只手拽住,另一只手从肩膀往手掌处捋。前面一次,后边一次地轮番捋着,捏着。
“我娃真心孝顺,可妈感觉不到啊!”
我说:“妈,我再来一次?”
母亲说:“你掐我?要不,你拿针攮,也行?”
我说:“那我就掐你?”母亲点点头,我用力掐了一下。母亲说:“我还试不着?”我从口袋摸出一根牙签,在母亲手背上扎一下。母亲说:“还是试不着呀?”如此十几分钟的按摩,捋搓、压、掐、扎,母亲全无反应。我说:“妈,这一次我回去,一定再给你抓十服中药,咱中西医一起来?”
母亲说:“每次来,你都给我用热水敷,亲手揉,使劲儿捏……可我就是感觉不到……这恐怕是要残废了?”说着,她就流眼泪。我说:“妈,你要有信心,我和妹妹一定把你的胳膊治好。那时候,就像从前,你给在场上妹妹晒药,看门,他俩种地养貂、养飞鼠。”
母亲越发地哭起来:“看着你妹妹妹夫在忙,我还要花钱。我就想早早死了算啦!”就这一句话,她哭,我哭,土房里哭声跌宕起伏。妹妹一把把门推开,说:“我就想着是你娘儿俩,哭吧,你儿子来了,好好哭一场,省得走了,今日要我打电话,明日要我捎信。”
妹夫进来了,他把小饭桌放在母亲面前,把葡萄、苹果和香蕉以及我带来的月饼打开,给我倒了一杯甜酒递到手中。
妹妹换了我,给母亲擦干眼泪,把头梳了扎住,在一个小碗里给母亲放了月饼,和葡萄和香蕉。
“妈,这是我哥给你买的,你尝尝?”
母亲就哽咽着,用左手在碗里捏起一颗葡萄,看一会儿,说:“建刚,你给妈喂?”我把葡萄一颗一颗轻轻放进母亲嘴里。
我说:“妈,葡萄甜吗……”
母亲说:“我娃买的,甜,甜……”
妹夫说:“妈,别哭了,我哥来啦,咱应该高兴。”
母亲说:“好,你哥来啦,应该高兴,应该高兴。”
“外婆,我来了?”呼喊声中外甥女来了,母亲说:“给娃葡萄,给娃葡萄!”外甥女接过妹夫递的葡萄和月饼,叫声外婆,舅舅再见,便出门玩耍去了。
屋子里,妹子给母亲搓手,揉胳膊。我和妹夫在一旁看着、学着。提前来到的中秋节,在母亲居住的大山坳中,携带一股股瓜果之香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