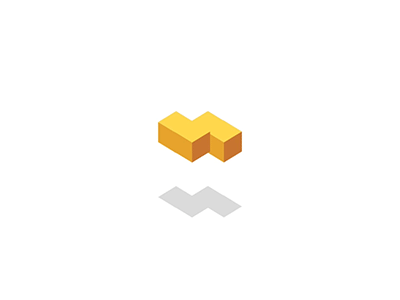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


三月已至,北方的春天来得并不隆重。灰蒙蒙的天空下,柳枝上努出几粒不起眼的“柳眼”。冷风如同锋利的刀片,从各角落猛烈出击,大街小巷再次删繁就简,一片肃然。
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我带着妈妈,行程六千里,裹挟着北国的寒,奔赴三亚,奔向大海,实现一个承诺。
快到机场了,飞机越来越低,透过机舱玻璃,一路连绵的丘陵沟壑,已变作无边无涯的大海。汹涌的海水,泛着白色的太阳光,光芒四射,灼灼逼人。妈妈探着身子,眼睛一眨不眨望向窗外,她是要把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尽收眼底吧。我热烈地拥着妈妈,紧紧地依偎着她瘦弱的身体。我和妈妈一样,两眼神采飞扬,俯视着下面的海,如同望着一个遥远的梦。梦想成真的快感,在我心间来回荡漾,以至于我忘了这个梦做了多久。能和妈妈做一个相同的梦,那一定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吧,时间啊,漫长得有些不合理了。
大海真好,它可以稀释我们的烦恼,可以抚慰生出的焦虑。出发前,对妈妈身体的担忧,此时,已化为乌有。
妈妈在太行山出生长大,工作后,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又一头钻进吕梁山。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已届不惑之年的她,才随同兵工厂走出大山,搬迁到城市。刚退休一年多,便得了脑梗,落下行动不便的后遗症。我的身体里流淌着她倔强的血,我懂得,一向不落人后的她,在突如其来的疾病前,她的痛苦是那样的令人愁肠百结。时间煎熬着她的心性,也煎熬着我们的期盼。终于有一天,她释然了,她歪斜着嘴,拖着不灵便的身体,对我们灿然微笑。
从此,吃饭时,她的嘴边经常挂着几粒米,固执地坚守每一餐饭。奇怪的是,每吃完饭,那几粒米就神奇地消失了,像从未出现过。对此,家人也从来当作没看见。妈妈只是病了,不是傻了。那时,她刚五十岁,她不愿意被人关注。如果为几粒米劳神,那得耽误多少事。
决定到三亚时,我才意识到,古稀之年的妈妈,竟没见过大海。
我不可思议地面对这个现实,如同突如其来的急刹车,被甩得不轻。因为过分震惊,我的心抽搐地一沉,泪眼蒙眬地盯看手机里订票成功的信息,才又燃起几分欣慰。好在,还不晚,这个春天,愿望就要实现了。
出了机场,悠长的蓝色甬道通向停车场方向。爸爸和出租车司机已穿过马路。妈妈背着蓝底黄碎花的双肩包,腐着腿,一拐一拐吃力前行。我要帮妈妈背包,她不同意。在蓝天白云椰林碧水之间,妈妈要充分享受这份恣意与欢畅的自由。她用一深一浅的双脚,感受着南国这片土地的坚实与辽远。
我跟在她后面。她单薄的后背上,储蓄着一团团温暖的阳光。何时,我也曾娇憨地把小脸贴在上面,微闭着双眼,享受一份独给我的爱。
在一些身不由己的日子里,在我还不记事时,曾经遇到与生死有关的事。在妈妈轻描淡写的讲述中,远离的日子又渐渐靠近,我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别人的故事。
那时我有多大,只能用几个月来表述我的岁数。爸爸出差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妈妈。睡到半夜,依稀听到房门被什么东西抓得唰唰响。妈妈惊醒了,她没有出声,安慰自己这是风声。在这个山多人少的地方,一到冬季,山里的风都很强硬,整夜乱窜。她知道,人不能和风较劲,就是吼破嗓子,风也不可能搭理她。她翻个身,想继续睡觉,但今晚这个声音明显有些不一样,隔着门板,都可以感觉到寒风中一双闪烁着幽绿的光的眼睛,这双眼睛就是两把锋利的匕首,闪着咄咄逼人的锐利。妈妈明白了什么,身子一下麻软了,她确信,外面不仅有风声,还可能有动物,它或它们正用尖爪抓挠房门。一阵慌乱,她的手触摸到我柔软的身子。我睡得正香,小鼻子一鼓一鼓,呼吸均匀。婴儿特有的恬淡,催发出她身体里的万千勇气,即便手无寸铁,也成了自己的英雄。她的嘴唇发干,眼睛湿润。她把屋子里唯一的桌子牢固靠在门后。虽然她和外面隔着一道门,一张桌子,在她看来,也只是隔着一块薄冰。她的一举一动都很郑重,都经过深思熟虑,她不能激怒门外的不速之客,更不可以惊醒我。
天还黑着,所有的人都没醒。时间一小步一小步迈过这间小屋,直到邻居的门响了,妈妈才跳下床,犹犹豫豫打开门。房门上,暧昧不清的印子,细碎的木屑,在亮堂的早晨,有些触目惊心,又有些不真实。
一种清凉触动着我,猛一抬头,我看见不远处黑压压一片,偶有几点灯火。那是大海。三亚的夜晚比白天更舒服。我和妈妈坐在阳台上,楼下的三角梅开得密不透风,三亚湾路灯火通明,沿街悬挂的红灯笼,半掩在茂密的绿叶里,残留着春节的余味。
这是别人的城市,这是另一种季节,这种感觉熟悉又陌生、亲切又如隔世,海水拍打在它无数次拍打的地方,热闹的音乐从繁密的椰林间响起。我和妈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没想到,这辈子,我还能跑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海。妈妈隐在她悄无声息的世界里,止不住的不可思议。年轻时,我最大愿望是到省城生活,后来实现了。大海呢,现在我就在它的旁边,看着它……
妈妈兴致很高,接着说,有次到省城学习,有人看不上我,以为我从山沟沟里出来,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有一次化验一种元素,他们不愿意教我。没想到,我做得比他们还好。那时,他们都服了……
妈妈笑了,歪着嘴。那是她的骄傲,从山里到城市的倔强。每个人,每件事,都在岁月的影子里缓缓伸长,伸到遥远的只有她才可以看到的地方,再慢慢返回到她的跟前。
我静静坐着,妈妈也静静的。过去的事,就像刚刚发生,就像我们还没有离开。有一阵子,她迷上了做衣服,她借阅了许多杂志,照猫画虎地裁剪,缝制。过不了多久,远在山外的我就收到妈妈寄来的衣服。我那时在老家生活。奶奶和我围在一起,惊喜地打量那些崭新的服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那个封闭的小县城,我竟没有勇气穿出去,它们过于新奇,过于时髦,与我周围同学的穿戴格格不入。我甚至纠结着想把那些腰带,或是蝴蝶结揪下来,企图还原它们的平凡。其实,我的心里装满了毛茸茸的五光十色,它们是妈妈带来的。
准备返程那日,我屋里屋外收拾行李。妈妈双臂倚着阳台栏杆,手里捏着一朵火红的木棉花,那是前一日在南山寺捡拾的。面朝大海,妈妈小声念叨:再见了……
这是她一个人的告别。
我永远看不到妈妈七岁时的模样,但我知道,七十岁的妈妈,仍有一份属于她的欢喜。如同七岁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