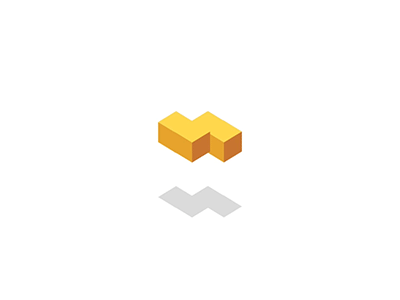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


叔父生病了,很严重,说是和父亲当时的病一样。我哭得很伤心,为叔父,也为父亲。
多少年了,从来不愿去打开有关父亲的记忆。
我在家里最小,是个不孝子。父母去世我都没在旁边,只有姐姐们零星的关于他们最后情形的描述。有时,我都记不清他们真的不在了。我常想,父母太爱我了,不忍心让我看到他们离世,怕我承受不了。也常常做同样的梦:爹妈坐在炕上,一边一个,我去洗了一大一小的酒杯,从柜里取出“柳林春”或“九成宫”酒,给他们倒上,慢慢品,妈常剩些在杯中让我喝。
妈走的早两年,那时整个家就垮了。家里人还没有从妈离世的痛苦中走出来,父亲就病了。
我没有照管过父亲一天,甚至没有机会说几句话。父亲走后很多年,逢年过节和家里人一起,才会提起他的点滴。每到这种时候,我总是拿别的话支开,要么起身离开,喉咙里就会有什么东西卡住。
但我一直想为他说些什么,他劳碌的一生,他暴躁的脾气,他苛刻地对人对己,以及他不为人知的细腻和多情。
父亲十九岁参加工作,那时全国还没解放。他曾和抓壮丁的碰到大门口,衣领已被抓住,挣脱后转身就跑,在荒山上待了三天三夜。他做过老师,后来在省公安厅时还参加过彭德怀元帅来西安的警卫工作。那时交通十分不便,也为了节省路费,常常走小路回家,要走两天,回到家时往往肩上有一捆柴。后来奶奶病了,他要求调回老家。他是他们姐妹的老大,又是孝子。他曾有过一个也许是这一生唯一的奢侈品,瑞士产的马蹄表,最后卖掉用于奶奶的药费了。父亲一生清廉,他的同事都尽力为自己的子女安排工作。他却说:“别指望我,靠自己。”妈妈常常气得没话。
回乡之后的父亲忙极了,好像在弥补他许多年对土地的亏欠。一年四季都在地里挖、锄。这还不够,还去开荒地,种药种菜种麦子种油菜。说实在的,父亲不是做庄稼的好手,以至每年收割时节,我们要跑遍整个山洼洼才能收回那些庄稼,还常常连种子都不够。哥哥们抱怨父亲是白费力气,他也不管,明年还是照旧。只有两次种菜获得了大丰收,一是白菜,一亩地,种在一条大路边,那年几个村的人都吃上了他种的大白菜,他本来计划拿去卖。还有是香菜,旺的能用镰刀割,家家户户都吃。家里人说你种了也不看住,让人拔光了,父亲一笑,“谁吃都一样”。他还喜欢种核桃,院子的两棵核桃树是他从新疆带回的品种,每年都拿几筐去山沟里种。现在山上、村里好多家都有这样的核桃树。
父亲对儿女的期望很高,他总认为生活好了,应该做得更好,但我们常常令他失望。他酷爱书法,有一个红铜质地的墨盒,两只狼毫笔,几本柳公权的字帖。他希望儿女都能练就一笔好字,我们每个人都在幼年时期接受过他的启蒙,但没有一个坚持下去。农闲时,他就在家里拿旧报纸练字,有时还握着我的手写几个。每逢村里谁家过红白事,他就拿上那套家当去帮忙,这时的父亲很神气。他也读书,最常读的是《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比较着看,高兴了还会大声朗读,惹得我们发笑。两个姐夫第一次上门,他便拿出书中的几段,让他们讲,他在考试。好在姐夫们全是师大的高才生,语文教师,顺利通过。轮到了我的一介武夫的男友,生怕过不了关,去家的前几日就惴惴不安,那次父亲却没有拿书来考,只淡淡问了几个问题。他对他的小女总有些许的偏爱。
娱乐活动对父亲来说是浪费时间,也不允许子女参与。下象棋也是偶尔为之,从不上瘾。村里那时也没什么娱乐的东西,就是象棋。大家公用的一副是年三十晚上他给那群淘气的孙子辈们发的压岁钱买的。他们跪了满满一地,吃的喝的都不要,专要钱,父亲特别高兴,给他们中的老大给了五十块,让拿去买棋。
父亲讲给我很多他年轻时的故事,大多都不记得了。只是有一次打猎,野猪已受重伤,但还在挣扎,他们就在山坳相持,走走停停几十里,都疲惫不堪,直到那野物血流光死了,父亲硬是给拖了回来。要知道,那时的一头野猪,顶一家十几口人几个月的生活费。父亲很疼爱他的弟妹,对他们的孩子也好,在经济上从不含糊。只是说话不多,也不注意方式,太耿直,太严厉,让他们都很畏惧。
那些年,父亲的工资都由一家大小瓜分,留到他手的已是不多,他从小节俭,总是舍不得给自己。他最怕浪费。大姐给他织个毛衣,招来一顿骂,一是他不需要,棉袄就行,二是浪费时间,学习要紧。我工作后给他买过一件短呢子大衣,倒是没挨骂。那时儿女们都自食其力了,没有压力了,他才接受。他最好的衣服是我参谋他出钱买的一套西装,很合身,配上表哥送的红领带,十分精神。我们一起去逛炎帝陵,照了很多照片。也是在那时,我才懂了父亲,一个在衣着上很有品位的人。
父亲是个极不会处理夫妻关系的大男子主义者。很多时候都会为极小的事与妈争,就像是搞工作,非要一清二楚。从小就当家的妈自然忍受不了,他们为此常生气。哥姐们没人愿意和他亲近,都认为是他的错。小时候我也十分怨恨他,觉得他对妈一点都不好。后来妈去照顾年迈的外公,每月只能回家十天。这十天就像家里的节日,我跳跳蹦蹦,父亲哼着小曲进进出出,一家人整齐鲜亮。爹妈年轻时分居两地,离多聚少,老了在一起自然会磕磕绊绊。父辈他们,有着自己生活的烙印,内心的东西很难看到,其实,他们是很眷恋对方的。有时父亲还会讲起年轻时领妈去西安,去乾陵逛的情形,而且总是滔滔不绝,好像是另一个父亲。妈有严重的风湿病,父亲每年让妈去蓝田或者汤浴温泉疗养,在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地方,这种事也是不多见的。父亲不善表达,别人也难理解。
父亲身体一直很好,连感冒都很少有,却突然病倒。真不敢想,那样健康的人,成天在外奔波,突然变得没法走出门,还要天天打针、吃药,他怎样去承受!那么坚强的人,被病痛折磨得在深夜痛哭,怎样能割舍他用一生的劳顿支撑的家、他爱的子孙!上天既有好生之德,为何要让人遭受如此磨难,一辈子受苦不够,临到离世还要把痛苦承受到极点!
总以为关于父亲,我会说很多很多。却寥寥几笔,就是他的一生。
多少年了,只有清明和“十一”,在大门外的十字路口,化几张写有爹妈名字的纸钱,祈福他们在那个世界温饱。旋成一堆的纸灰,绕着身体飞舞,就像和他们相拥。
父亲不是父亲中的楷模,却如地头簇簇迎风的香菜,飘着淡淡的幽香,让喜欢它的人,尽情享受生的快乐,再也无法忘掉它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