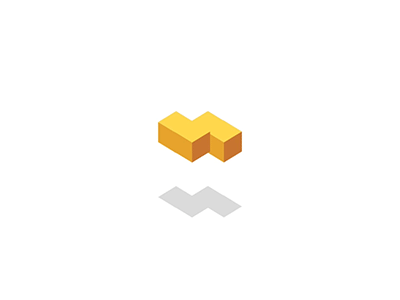前些时候,我创作的一件临水式盆景作品题名为《在水一方》。有朋友打听出处,我回应取自《诗经.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提起蒹葭,蒹葭可以泛指芦苇。芦苇是可用之材,可以编席、筐、篮、宫灯、屏风等日用品和工艺品;可以造纸,作建筑材料。芦穗能够扎扫帚,芦花能够填枕头,芦根能够入药。我在农村劳动时就干过斫芦苇的活儿,收割起来加以利用。芦苇荡如沙家浜、白洋淀等曾经是抗日杀敌的好战场。蒹葭也引发多少文人墨客托物言志,几多诗情画意:你看她亭亭玉立,婀娜妩媚,一丛丛、一片片,迎风摇曳,姿态万千,质朴无华,野趣横生,还每每藏着几只兔子,时而惊起一群鸟儿。
然而,蒹葭啊芦苇,50年前却深深刺痛我稚嫩的心灵。
1968年我初中毕业两年后正式离校回乡劳动,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之时。有一天晚上,生产队里开大会,我也被通知参加了。哪料到“文化大革命”没有世外桃源,农村也不能幸免于难。到会场后有人悄悄地告诉我,会议的内容是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队长、会计的滔天罪行。生产队长、会计难道也手握大权罪大恶极?古时县令才是七品芝麻官,不知当代生产队干部能算粉末官吗?我心中大惑不解。我的父亲是会计,任职许多年了。他白天上工,晴天、阴天上工,夜晚和雨天记账、算账,勤勤恳恳,深得群众拥戴。会议开始前,社员们坐在那里叽叽喳喳地聊天,对开会似乎不感兴趣。
突然,听到一声断喝:“顾某某、于某某站起来!”
大家都被镇住了,顿时鸦雀无声,我的心里一紧。队长顾某某和我的父亲于某某像触电似地直直地竖起来,露出惊恐、惶惑的目光,因寻找声音来源而下意识昂着的头颅被强行按下。
又听一声叱喝:“顾某某、于某某老实交代罪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的父亲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交代,说账目可以任意查,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其实,他心中有数,账目上没有任何问题,实际上早就被查过没有被查出什么问题。造反派的几个年轻人认定他态度恶劣,上去施以一顿拳打脚踢。有一个人凶神恶煞地嗔喝一声:“屎缸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接着,揭发了一桩匪夷所思关于芦头(芦苇在当地称芦头)的事。
我们公社开展水利建设,有一条母亲河——沧河疏浚拓宽,我家的一座房屋阻碍到了,必须拆迁。那时物资匮乏,许多生活用品、生产资料都凭计划供应,拆迁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优惠政策,只有很少一点补偿。我家三、四间房子只象征性地补偿了200元钱和600块砖头、800斤江边芦头的计划。这芦头是给编织望帐盖屋顶用的。长在江边的芦头比我们当地长在沟岸的芦头质量差得很多,矮、细、软,皮壳薄。运回来一看,根本不能用来编织望帐盖屋顶,不堪上面泥巴和厚厚稻草的重负。我的父亲就把江边芦头拉到自由市场(当时被称为黑市)上卖给手艺人做不需承重较大的芦菲、畚箕。后来又以比江芦高出许多的价格买了一些当地沟岸上又高又粗又硬、皮壳厚的芦头。因为经济拮据,只能买少量的用来修补旧的望帐。
“套取国家计划物资,投机倒把,你知罪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父亲有口难辩,冤枉啊!我坐在那里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害怕,瑟瑟发抖,根本没有胆量站出来辩护,其实人微言轻,也没有我说话的份儿。在学校由于年龄偏小,又在农村长大,胆小怕事,在许多文斗加武斗“轰轰烈烈”的场合,我只是个旁观者、逍遥派。最后,生产队的几个造反派战士不容分说,无需集体讨论,更不必法庭审理,我父亲的“罪名”就被定下了,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幸好再无法给予什么处分(我的父亲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家干部),更无法判定什么徒刑。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睹物思事,触景生情,对那件关于芦苇的事耿耿于怀,在芦苇上蒙罩了一层阴影久久未曾散去,直至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后。我看见芦苇还是那芦苇,蒹葭还是那蒹葭,临水而立,光摇雁栖,好像在习习清风中列队向人们颔首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