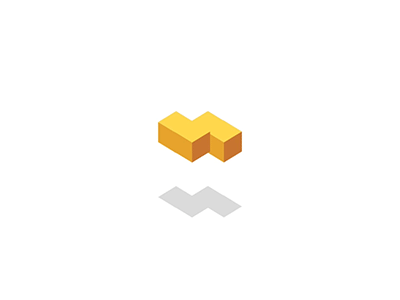因疫情原因,我三个月没能回老家。在农历三月底的一个周末,终于可以回家探望父亲了。
父亲已八十六岁了,花白的头发,驼着背,因为腰疼的缘故,走路时身体向一侧倾斜着。父亲一见到我,满是皱纹的脸上堆满了笑意,布满血丝的眼睛也发着光。每次见到父亲,我总是把带来的好东西一股脑地拿出来,一件一件地让父亲看,让他高兴高兴。这次也不例外。当看到我买的外套时,长叹着说“我有的是衣服啊,怎么又买了,我死了,这些给谁穿呢,白白浪费钱!”边说边弯下腰,从床底下拖出三个纸箱子来。纸箱子里全是半新不旧的衣服,有的已经缝过了,但叠得很整齐。父亲扒拉着里面的衣服,炫富般地说:“你看,你看,有多少衣服了吧”,我说:“你把太旧的扔了吧,只穿好的”,“这些没一个打过补丁的!”父亲看到一件件衣服,便开始如数家珍似的诉说着它的来历,“这件夹袄(带里子的外套)是十八年前去泰安你那,小李子(我老公)给我买的,那时你娘还在,九十九块钱买的,这件衣服真舒服啊,别的褂子洗了一会儿就干了,这个可不容易干”,“这个围巾是上东北卖地瓜的时候,东北你婶婶发现我脸上冻起了疙瘩,一晚上织成的”,“这条裤子,是和你大爷赶集的时候十块钱买的”,“唉,你婶婶你大爷你娘都走了”.....我静静地听着,这已经不单单是衣服了,俨然已成了记忆的闸门,每件衣服都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父亲从小没了我爷爷,跟着我奶奶,靠买豆腐生活,吃尽了苦头。后来养育了七个孩子,唯一的男孩是最小的弟弟。大姐二姐在公社小队里干活,一人一天只挣半个工分。父亲在副业队干会计。挣的工分少,年年没余粮。过怕了穷日子的父亲勤俭了一辈子,谁乱扔东西,他就跟谁急。
我每次返程的时候,父亲总是给我带上好吃的。有花生的时候,就带上一大包花生;种葱的时候,就给一捆大葱;摘了新鲜的蔬菜,就给一篮子菜,反正不让空着手。这次既没有花生,也没有大葱,更没有菜了,父亲四下里瞅着,发现了半箱字鸡蛋,非让我带上不可,那可是他最爱吃的东西啊。“一路上会碰烂的”我说,“那带几个熟的吧,孩子虽然大了,但也是孩子啊,盼着吃姥爷的好东西呢”父亲说着。却之不恭了,那就煮吧。等我回到厨房的时候,父亲已经煮好了,打开锅盖,白的红的,满满的一汤锅鸡蛋,足足有六七斤。“爹,吃不了啊,会坏的”,“你家不是有冰箱吗?”父亲以为冰箱是个神奇的大冷库,什么东西只要放进冰箱里,便永远坏不了。
看着白花花的鸡蛋,我的眼睛模糊了。记得上学的时候,只要大考,父亲便给我带来煮鸡蛋,也许那是最快最好的补充营养的方法吧。
高中时期,学习很紧张,我四周才能回家一次。平时都是父亲给我送饭,父亲实在不得闲的时候,请赶集的同村人给我捎过来。一顿饭三张煎饼,一周六十三张,不能多吃,不然得有挨饿的时候。这么多煎饼,加几瓶炒咸菜,煎豆腐,偶尔也有芹菜炒肉丝,一篮子满满的。
在我记忆里,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是初夏的那次送饭。
那是农历五月初的一个清晨,天蒙蒙亮(初夏,天亮的很早,也就四点多吧),同宿舍三十几号人都在睡梦中。忽然,听得有人轻轻敲门,小声地叫着我的名字,开门一看,门外果然是父亲。三十里的盘山公路,骑自行车也得一个多小时。抹黑赶来了,的确让人很吃惊。父亲的脸上头发上湿漉漉的,搓着两手,瑟缩着,嘴里哈着热气,臂弯里挎着篮子,鼓鼓的,身边停放着一辆自行车。我连忙让父亲进屋暖和暖和,他不肯进,说不方便。同学们早已醒了过来,满屋子充满了唏嘘感叹声,“哎呀,这么早啊!”“大爷,快进来喝点热水吧,外面太冷了”。父亲应着声,放下东西,叮嘱我几句,转身就要走。“爹,歇会吧,吃了饭再走”,“家里等我割麦子呢,都约好人了”。话音刚落,父亲骑上自行车,消失在晨雾里。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眼.....
因家庭贫困,每次要交学杂费的时候,我都要掂量好几遍,不好意思开口。父亲却从不拖欠,总是第二天就把钱准备好了,看到我欢天喜地地拿着钱走了,他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所幸的是,父亲有个手艺,会用白藤条编篮字。一个篮字能卖六块钱。藤条易脆,编之前,需把藤条泡上一整天。为保持空气湿润,只能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作业。冬天,地窖里冷飕飕的。没有电灯,用煤油灯照明。地窖没有窗子,只有一个洞口,盖得严严的,通风不好。煤油灯的烟都吸进了嘴里肺里。父亲的鼻子喉咙里全是黑灰,吐出的都是黑黑的浓痰。父亲总是鸡叫两遍便起床了(凌晨3点左右),然后是奋力的咳嗽声,那撕心裂肺般的声音,让人心里一阵阵地难受。
父亲也有攀比心,总希望我也能像村里某某一样考上大学,便光宗耀祖了。父亲的期望给了我无形的压力,也给了我无穷的动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是一往无前。
父爱如山。父亲给我的爱总是暖在心里。当我知道,世上还有个年迈的父亲在牵挂着我的时候,我便不再孤单。
注:本文已经在《散文百家》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