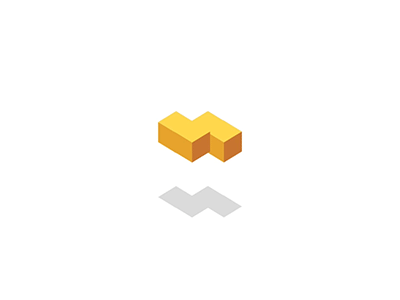包头 东北大青山北麓,有一处开阔的小盆地,黄河支流五当沟将东西村划为S形轮廓,一分为二又合而为一。从高空俯视,活脱一幅河川田地阴阳太极图。包涵于大青山南北向支脉间。
西村南头一个小山上,生长一棵千年老榆,向东一枝离地一米多高平伸出去,水桶粗细,二丈余长,形似迎客伸臂握手。“爬榆树”村名由此而得,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
民国年间,走西口先民来此定居,在这个古代少数民族的游牧地开荒务农。山上树木葱笼、河滩草花遍地。溪水由山而出,在草皮植被上淙淙流淌。随着人畜的增长,土地扩大,山林草地减少。遇旱年粮食不济,人畜皆以野菜树皮充饥,生态逐步失衡。山上树草稀疏,河滩沙石裸露,每逢大雨,水土流失,泥沙俱下,黑土被洪水冲涮夹带而去。前山人就说:“后山一声雷,添土又添肥”。
上世纪六十年代,部分移民迁来,五当沟流域村庄遍布。经过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运动,人们过量向山川土地索取,自然生态进一步恶化。生活生产几乎难以为继。
1964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各村砌石筑堰,运土造地,打井开渠,大搞农田基础建设。
爬榆树大队领导班子提出“因地制宜学大寨”。誓将“S”形弯里的东西河滩变成良田。先把平滩的石头搬到河沿筑拦洪大坝,再在坝内每十亩东西走向挖土打堰,然后开引洪大渠,等山洪下来引洪水进堰澄淤泥肥造地。最后解决水源灌溉。
艰苦大干,扩大良田水地一千亩。其间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回村劳动。父母被错误的戴上“黑五类”帽子,干最苦重的农活。我被指派去垒拦洪石坝。两人抬起石块放在背上,我咬牙挺腰支撑着,双腿索索抖颤地向前移动。如果倒下则伤残甚至丧命。这种活儿一般是秋收后干起一直到次年春耕。
数九寒天,北风刺骨,黄沙土卷起,钻入五官七窍衣领之内。双手麻木、抠紧石头不敢松劲,水泡磨破结起厚茧,手背划伤血染石头。从日上一竿出工到夕阳落山,午间歇息吃玉米面窝头就凉水,晚上回家喝菜稀粥。骨软肉疼,腰膝酸麻。放下饭碗赶忙起身去替父母挖土培堰塄做额外的赎罪劳动。干上三个小时回家。肚中饥饿,无食可吃,疲累睡下,酣然入梦。过份繁重的体力劳动,使灵感窒息,心灵麻木。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来下地做早饭,多数是土豆腌酸菜汤再加两把玉米面成糊状,另给父亲和我烙两块玉米面加细糠饼,以补体力。母亲开始生火时我就醒了,从枕头下面抽出那本只剩一半封皮四角卷起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继续上次读到的页码往下读。
沙滩和河槽表面的石头用完后,垒石坝的留下两三个人,其余人都到对面山上采石头,我们手握铁撬棍,先把松动的掀起滚下山,然后再打眼儿装炸药开山取石。我手握木柄挥舞着十磅的铁锤,砸在另一个人掌握的铁钎面上,开头小心翼翼,生怕走偏砸在人的手或胳膊上。慢慢熟练,稳准有力,随着“叮噔”之声,眼孔渐渐加深。到七八十公分时就可装炸药安雷管引爆。一声巨响,地动山摇,灰尘腾空,数十吨石头瞬间被剥离山体,碎裂成大大小小的石块轰隆隆滚下山坡。我们将石块抬上三套骡马胶轮大车,拉往工地。
夏天,大雨倾盆,上游几条山沟洪水暴发,水头一米多高的柴草腐殖质畜粪如几排黑骏马奔腾而下,发出闷雷般的轰鸣。大雨就是警钟,洪水就是命令,全村男女老少抱着麦秸草捆,扛着木桩篱笆,发疯般奔向河沿渠口,等洪峰溢流入渠,一小队社员跟水进入打筑好堰塄的荒地,引导分水。带着群山沃土的黑稠洪水从头一个堰地东口进入,转弯分散又汇聚到第二堰地的西口,便澄下一部分泥土,一直旋流完十几个堰地,泥土肥料绝大部分沉淀在沙滩地上,平均三四寸厚。不大一会儿,大河槽洪水变小平稳,几十名青壮年扛桩抱草手拉手进到洪水中,挪步向河心打桩下篱笆堵草捆。齐大腿深的水时刻会将人冲倒卷走,凝视水面,人如逆流而上。必须立定脚跟,步步谨慎。山洪越来越小, 拦洪队伍抵达对岸,将洪水全部拦入大渠流进堰地。后山的表土肥料就凭借山洪转移到我村的荒滩里。二三年后,积土一尺左右,便可耕种。也减少了流入黄河的泥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