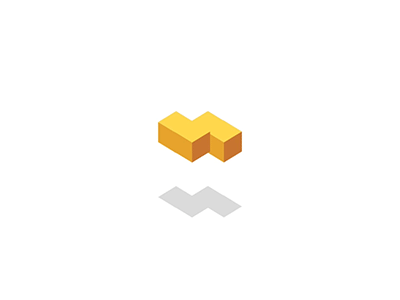潘家园是北京新兴的一座文化地标。我这么说,大凡热爱收藏,喜欢古董、字画的玩家都会认同。其实,潘家园一带形成文化产业聚集区时间并不长,也就二十年的样子。在过去,北京只有琉璃厂,那才是正八经的去处。琉璃厂有大名鼎鼎的荣宝斋,有无数的文房铺子,包括书店。
印象中,潘家园最早发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经商热。经商热是紧随下海热的,那下海热呢,则紧随着下岗热。大约1987年前后,人们还好端端的上班呢,不管是国营还是大集体,干劲儿十足,可谁知,老天爷突然变了脸,一夜之间许多工厂纷纷搞起了砸三铁。您要问哪三铁,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呗。
潘家园附近有几家国营大厂,北京内燃机总厂、人民机械厂、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北京东风无线电厂,稍远点的还有北京化工厂、焦化厂、染料厂,至于几百人的工厂就数不过来了。这些产业工人加起来,不会少于二三十万吧。
当时的媒体,或者说政府主管部门,还不敢用下岗这个刺激的新名词,而是用分流用市场疲软用三角债给予解释。但不管怎么说,工人终究是下了岗了。我是九十年代初进入到新创刊的《北京工人报》做记者的。记得刚创刊那天,是在深冬,我和几个同事每个人抱着200张报纸到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口免费向行人发放,嘴里还不忘吆喝着”快来看啊,新创刊的《北京工人报》,首都360万工人自己的报啊”,可是,白吆喝了半天,没有一个人主动跟我要报纸的。后来,我见一个戴着眼镜有点机关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就走过去主动往他手里塞,哪知那老兄一听是工人报,马上就把报纸塞还给我,嘴里还很高贵的说道:”不看不看,我怎么能看这样的报纸”!瞬间,我觉得我的血液都凝固了,自己太没面儿了,真想把那家伙叫回来,狠狠地教训他一顿,质问他穿的衣服、皮鞋,戴的眼镜是不是工人生产的。没有工人,大冬天的你喝西北风去吧。可联想到当时产业工人的处境,也实在不好说什么。
两个月后,快到春节了,报社让报选题。我提出采访几家严重亏损的大中型企业,特别提出到北京手表厂,采访他们是如何兼并北京针织六厂的。据我了解,由于受海湾战争的影响,针织六厂已经连续几年亏损,最近半年接连换了三任厂长,现在的厂长由一名女工程师代理,女厂长跟纺织局领导提出,只干三个月,过了三个月爱谁干谁干。这期间,中央某领导提出鱼和熊掌可以二者兼得,提倡企业间可以兼并重组。这样,就出现了经济效益较好的北京手表厂兼并针织六厂的典型范例。而另一名记者则提出,到潘家园鬼市去采访跳蚤市场的情况。所谓鬼市、跳蚤市场,就是一些下岗工人从工厂家里拿一些服装、百货、旧物早晨或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进行交易的场所。我记得在九十年代,这样的市场在京城里有很多家,只不过潘家园的比较有名就是了。
对于我们的选题,报社领导都觉得很好。这样,第二天我们就兵分两路去采访。原计划每个人采访两天,后天交稿,然而,当我们真的深入到企业和跳蚤市场后,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北京手表厂在郊区昌平一带,我记得我们家曾经买过两块他们的双菱牌手表,那表虽然比不上老上海,可戴在一般人手腕上,也足让人羡慕的。我采访企业领导,跟他们谈企业重组,他们并没有那么兴奋,甚至有些无奈。其潜台词是,他们并不同意企业兼并重组,因为他们的收入也就勉强开工资。如果非让他们兼并针织六厂,那等于是死鸡拉活雁,既救不了你也救不了我。可市里和中央决定了,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主要目的是起个表率作用。尽管如此,我还得硬着头皮写,不写,怎么向报社向市里交代呢!
去潘家园的同事回来也不乐观。他们早晨五点多就去了,那时市场还没有形成,四周一片漆黑,人们在立交桥边自动的摆起了摊位,由于天还没有亮,摊主们各自打着手电筒,一闪一闪的,从远处看,就像坟地里的冥火。地摊上卖的物品有针织品,小百货,也有玉器、瓷器等手把件的,但字画还不多。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还是讲诚信的,所以,这里卖的东西基本是真的。偶尔有人走眼了,也没得怨,这就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起初,人们对跳蚤市场议论纷纷,说这跟投机倒把没什么两样。也有人说,这些下岗工人、无业游民整天的混在一起,容易引起社会动乱,建议公安工商介入,坚决给予取缔。一个摊主说,我们很不容易,早晨四点多就起来占地方,赶上点子正,可以买个三五十,如果点子背,一早晨也没个进项。说得更惨的,说有一天大伙正在卖货,忽然有人说工商的人来了,人们赶忙猫腰收拾东西,有的人甚至提溜着裤子到处乱跑,跟流氓似的,极其不雅。报社领导问,当地街道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譬如正式弄个市场什么的?同事说,好像有这个想法,但涉及的部门比较多,得慢慢来。
按照报社的要求,我们把文章都写好了。可领导说,这两篇文章不宜公开发表,只做内参上交到市总工会,再报到北京市委。至于市里怎么决定,我们只能是服从。当然,我们的文章不会白写,照样计入工作量。面对这样的决定,开始我还想争论几句,认为媒体就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如果不这样,问题就不会得到很快的解决。领导毕竟吃的咸盐比我们多,说,新闻无禁区,但发表有纪律。这是红线。
半年后,我离开了这家刚创刊不久的报社。二十年后,《北京工人报》更名为《劳动午报》,据说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我很感念这家报社的几位领导,是他们把我从农场调到这里,由此成为一名职业的新闻工作者。2012年,当我的一篇文艺评论获得第22届中国新闻奖时,我的内心还是相当激动的。记得那天我从京西宾馆出来,走在喧闹的长安街上,我多想对着天空喊一嗓子,我成功啦!然而,刹那间,我又终止了这样的荒唐的冲动,我问自己,你真的成功了吗?如果那一纸证书就证明你成功了,该有多么可笑。要知道,在长安街奔流不息的人群中,不知有多少人,人家在不同的行业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果都喊成功,中国梦不早就实现了吗?
潘家园旧货交易市场成立后,我断断续续去过几次。1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陪我侄子去潘家园买刻章的石料。没想到,遇到我八十年代在朝阳区文化馆一起学习的文友老田。老田原在酒仙桥一家国营大厂工作,当过销售科长,为人精明又不乏实在。老田告诉我,企业不景气,他提前办了内退,家就在附近,他没事喜欢逛潘家园,久而久之,就对石头、玉器来了兴趣。后来,他干脆在杂项市场也租了个摊位,卖起小文玩。我问他发财没有,老田一笑,说,发什么财?随便玩玩而已。我又问老田,小说还写吗?老田说,早就不写了,写出来也没地方发表啊。我劝老田,别灰心,你的京味儿语言那么好,只要题材对路子,不愁没地方发表。老田人很讲义气,给我侄子一大塑料袋的石头。那些石头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鸡血石、蓝田石、寿山石,但已足够我侄子学习用的。
跟老田重逢后,我们联系便多了起来。我帮他先后到几家报刊做文字工作,也介绍一些写作的活儿给他,挣钱多少不说,主要是想让他开阔一下视野。大约四五年前,老田一天突然找到我,说他现在特有写作的冲动。我说,我就等你这个感觉呢。我早就把你写作的题材帮你设计好了。老田瞪着一双牛眼望着我,说你赶紧告诉我。我说,你听好了,三年内别的什么都不要写,你就写潘家园风情录,系列中篇小说。如果你能写出十个八个,我保证你出大名。到时,我不仅帮你联系出版社出版,还帮你开研讨会。老田一听,心情很振奋,他说就这么定了。
自从听了我的话,老田就不再去潘家园练摊儿了。他一门心思写他的潘家园系列。果然,在不到一年时间,他陆续写出了三篇,其中第一篇我给推荐到《鄂尔多斯-小说精选》发表。后来,这篇小说还获得天津”文化杯”梁斌小说奖二等奖。有了这篇小说垫底,老田逐渐来了感觉,他又陆续写了几个中篇,只可惜不是潘家园题材的。这让我有点遗憾。还好,他的《天桥葛爷》等三篇以自然投稿被《北京文学》看中,先后发表,还被《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转载。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去年元旦刚过,传来老田因突发脑溢血去世的消息。我听后感觉头都大了,这怎么可能?前年老田还能骑自行车到天津呢!可是,接连几个朋友告诉我同一个消息,让你不得不相信。也许,这就是一个人的命运。
后来,我见到《北京文学》的编辑王秀云,聊天中得知是她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老田,并极力向主编推荐的。特别是在老田去世后,他们还发表了老田的一篇遗作。我说,老田要是地下有知,他也该知足了。我记得老田生前多次对我说,他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在《北京文学》发表作品,另一个是加入北京作家协会。如今,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他却匆匆走了。我有时在想,人干嘛走得那么急呢?这人世间还有多少快乐等待我们去享受呢?
前几日,黑龙江的一位文友来北京,让我陪他去逛潘家园。我们逛了两个多小时,也没什么可买的。走到文玩杂项市场,在昔日老田练摊儿的那个地方,有位藏民打扮的阿妈,她手里摇着转经筒,两眼直直地看着过往的行人,好像在寻找等待什么。我猜想,老阿妈是在寻找她的孩子吗?或者是在寻找买家?猛地,我想到老田,说不定她真的在寻找等待老田呢?因为,以老田的性格,他有可能跟这位老阿妈交上朋友的。本来,我想上前问问老阿妈在等什么人,可我看着她僵硬的眼神,感觉她不会跟我说话。道理很简单,我终究不是她要寻找要等待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