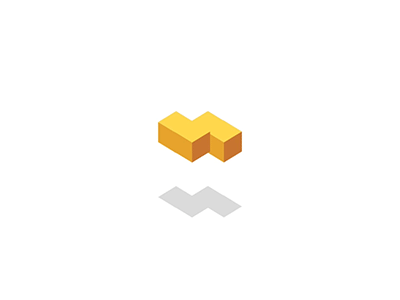位于自流井遗址下游约五百米的路边井最初是一口老盐井。她北接郭家坳的各大盐场井灶;南抵釜溪河边的运盐码头、张家沱、火神庙;东临釜溪河;西靠牛屎山。已经没有谁知道路边井开凿的具体年代了,也没谁知道她见功于那朝那代,盐井的主人是谁。甚至“因路凿井,还是因井设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像关于鸡和蛋的起源之说,成了一个千古之迷。人们只知道在若干年前,一位凿井的东家在今人称之为“逸园”的地方为打这口井,耗时十多年,钻井数百丈凿穿见到了黄卤。于是有了路边井。
清朝咸丰年间,路边井一带可热闹得很。那时这里天车林立,灶火兴盛。通洪、崇福、龙旺、宝龙、浮海诸井相继见功。随之而来,盐场井灶所需的铁匠铺,乒乒乓乓的铁具敲打声便此起彼伏的响亮起来;卖鸡婆头、豆花饭、猪肉、油盐酱醋、大米、药材等物品的店面前人来人往。在这青砖灰瓦之间,在这条宽不过两米的石板路上,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贾、盐贩,一批批一队队的沿着这条路,牵着叮噹作响骡子或者马匹,周而复始地往返,他们时常在这里随意的找个客栈暂住下来。“抬盐匠”、“白水工”、“转盐匠”、“烧盐匠”以及操着南腔北调的各地方的盐贩子,时常在这喧嚷的茶肆、酒馆里猜拳行令,小酌两杯;或者来一碗“盖碗儿”茶,在袅袅的茶香里慢慢地品味着上桥石板上那块关于神仙石的传说;路边井的陈年旧事;“张家沱的水狸子和马儿”的黄段子。这在他们是人生中令人惬意的事情了。
一条长约1.5公里的石板路逶迤在路边井,她连接着釜溪河西岸的各大盐场;连接着古老的运盐码头;她仿佛就是一根经脉把这一个个老盐场与大江南北的连接起来。这根经脉也是那些“抬盐匠”用晶莹的、咸涩的汗水淌出来的。在这条石板路上,长年奔走着那些身强力壮的“抬盐匠”。他们在这条石板路上,头上粘满了雪花般的盐沫,赤膊黝黑的上体,流淌着透亮的热汗一路吆喝着来回奔忙。似乎看上去劳作的时间并不算长,一般是半天的“活路”,但是满满140公斤左右重的“花盐”、“锅巴盐”“包子盐”借一根粗大的木杠子分在两个人的肩上,那远不是身小体弱的人所能承受的,即便是半天,也会让这些五大三粗的汉子精疲力竭。他们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那赖以生存的一升米而已。盐场的老板都是精明人,他们不会把“抬盐匠”雇用为长工,他们非常聪明的以“计件”的方式挑剔这些靠力气生活的抬盐匠。
这地方,这井和这路,由于晶莹的咸涩的半透明状颗粒——井盐——而常常被老人们提起。在这块肥沃的土地深处蕴含了丰富的井盐,于是有了群居于此的人,有了明清风格错落有致的串架的老房子,有了这些木质的小楼,有了这一扇扇褐色的宽大的木门,以及这条逶迤在釜溪河畔的石板路,它们至今仿佛还在向人们诉说着那久远的往事。
二
1938年4月,一个科考摄影队来到了自流井。孙明经,这位来自金陵大学的电影摄影教授,这位中国电影摄影、科考的创始人,带着一架6毫米的摄影机、一台120相机和他的助手范厚勤两人组成的摄影队来到了自流井。
一个晴好的下午,他漫步在路边井这条古老的石板路上。缓缓向南流淌的釜溪河水面停泊着几只木船。这船,老盐场的人叫它“歪脑壳”船。它们正闲着。一条顺流淌在波光之中;另一条靠在岸边,和那些撑着“蒿竿”往返漂泊在釜溪河上的撑船工人一样,终于回家有了片刻的小憩。弓着腰的洗衣女子涤荡着手里的衣物。一座被称为上桥的石板桥上人影晃动。对岸远处山颠上,那些典雅的小洋房仿佛它的主人,透过眼睛一般的窗户,似睁似闭的斜视着眼底的一切。阳光从西天洒下来,它把逶迤于近处的青石板路分野成明亮和阴暗两条对立的路影,把稀疏的行人留在里面。
这是一幅恬静、淡雅的,活活脱脱的舒展在三十年代末自流井釜溪河畔的真实的画面。孙明经这位时年27岁年青的学者多么向往这样恬淡的生活呀,他抬起了手里的相机,把那一瞬间从心灵淌出的情愫永远的留在了路边井这条石板路上。他知道这是难得的,也许是暂时的。或许不久之后,战火的浓烟将吞噬这里的宁静。
1937年7月7日夜晚,随着中国芦沟桥沉闷的炮声,中国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被笼罩在了一片战争的硝烟里。东北沦陷、南京沦陷、上海沦陷、昆明告急。长芦、山东、淮北等产盐区先后被占领,全国大部分产盐区被日军控制,海盐内运受阻。那些为了民族而战的前线将士和华中、西南、西北、两湖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面临着“无盐淡食”的困境。日军企图以切断食盐来源来消解中国军队,中国人民的战斗力、自信心。食盐,这个简单的非常平常的东西,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决定着生存,力量;与一个民族的存亡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孙明经先生带着摄影和摄像器材,告别已怀有身孕的妻子来到自流井。他是来考察自流井井盐生产状况的。他要通过拍摄自流井井盐生产的庞大规模,来为前线浴血奋战中的将士鼓劲,让正在遭受战火涂炭的名民众免受“无盐淡食”的困扰。三个月后,他带着让国人为之振奋的两部电影——《自贡井盐》、《井盐工业》——和大量的影像资料,离开了自流井,离开了路边井这条古老的石板路。
1939年9月1日,一份由中国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中正签署的关于在自流井老盐场成立自贡市的批文传至自流井。自贡市正式成立了。这是一个为了抗战而建立的,为了民族存亡而建立的城市,为了井盐的开采、增产、为了在战时广大地区军民有足够的食盐而建立的。
年产五六百万担食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釜溪河畔的各大盐场沸腾起来了。采卤工人没日没夜的忙碌在井口;烧盐匠加班加点熬制盐卤,路边井这条古老的石板路上,那些不管春夏秋冬,肩搭汗帕的抬盐匠赤胸露背一路吆喝着,奔忙着。他们厚实的肩膀上扛的不仅是不140公斤重的食盐,他们更承受着比这盐更深、更广、更沉的重量。这白花花半透明的晶体,这钻石一般闪着银光,给生命增添了神奇力量的井盐,就这样从路边井这条朴实的石板路运往川、康、滇、黔、湘、鄂、陕等诸省的几十个市地州,给战火硝烟里的勇士带去了信心和力量。
日本军国主义的疯子,那些试图细蛇吞大象般的傻瓜恼怒了,手握一把淌着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刀在叽里呱啦的怪叫声里,指向了自贡——这座新兴的城市。一阵阵蝗虫般的轰炸机铺天盖地把成千上万的重磅炸弹、燃烧弹从尖利的嘶叫声里疯狂地倾泻下来。牛屎山的老街被炸成了“光大街”,连接石板路的郭家坳产盐区18个井、灶、枧被身于火海浓烟之中,复兴炭灶、是洪井、新记大同枧等惨遭破坏。但是,这没能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屈服,几乎所有的人依然通宵达旦的忙碌着,他们把所有愤怒、不屈的反击都化作一袋袋,一坨坨,一船又一船的闪着银光的食盐,化作“像一个很大的炸弹,飞到东京去,炸翻了日寇的东条内阁”。东条下台了。
三
而今的路边井是宁静的。
这宁静是从大地底层、从上桥釜溪河的底部漫漫升起来的。它化作淡淡的岚雾,寂然悬垂在水面然后飘荡开去,顺着河边的崖壁,顺着这条石板路延展,静默的弥漫、淹没这古朴的房屋、小楼和散发着古木幽香的店铺。
夜在无声的融化着这里的山、水,这飞檐翘角的老房子。一位满脸沧桑的老者,艰难的拄着手杖顺着石板路向着巷子的深处远去,最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这时,一株绿草从他消失的地方,在房檐屋顶伫立起来,在凛冽的寒风里久久的颤栗。
——《龙乡文学》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