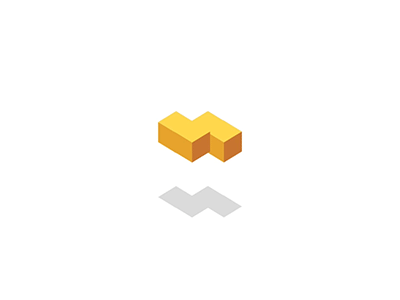十七岁,是人生的花季,五彩斑斓;十七岁,也是一个少年对未来的畅想;十七岁,我的人生定格在北京海军司令部警卫二连。
经过两个月的新兵集训后,于1981年1月初我被分配到海军司令部警卫二连三排七班。岁月无情,尽管时光过去了四十年,我已记不全当时班里所有战士的名字,但还能依稀记得几位:唐精忠班长、张玉强、秦国富、李富怀、王柄民、王泉、荣晋宝。唐精忠班长提干后后来到海军政治部工作,我们隔三差五能见面,至今还比较熟稔;张玉强是浙江老乡,他退役后直至2017年在萧山战友见面会上遇见;秦国富后来在海军大院4号楼见过,当时他生病了,此后就杳如黄鹤了;其他几位战友自我离开警卫二连后就无联系了。
那时的警卫二连营区位于海军大院东北角,紧靠公主坟大转盘,东临1路与4路公交车始发站。二连的营房主体由三排平房构成:第一排是食堂、炊事班,还有仓库;第二排东侧是连部,隔一间弄堂,西侧是一排三个班;第三排西侧是二排的三个班,东侧是三排的三个班。第三排营房北面留数米宽的隔离区就是海军大院的北围墙,墙的外面就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复兴路。刚下到七班晚上睡觉时,发现屋子里的灯虽然是关了,但窗外路灯射进来的光线还是把室内照得明晃晃,给屋子增添了几分迷离与遐想。睡在床上,床底下传来一阵一阵有节奏的隆隆的机车声,开始感到迷惑,后来才知道,那是地铁从房子底下驶过。起先对这种声音并不习惯,于是在不久的一个晚上做了一个恶梦,把战士们都吵醒了,第二天起床时,大家议论纷纷。
在七班这个集体里,呆的时间不长,大概不到半年,但给我留下了些许精彩的瞬间。
三排负责海军大院东大门的警卫任务,每班次两个战士。有一天晚上,我与张玉强站岗。那时,轮到上岗的战士出发前都在连部西侧的弄堂集合,然后走向各个岗哨。我与张玉强经过营区东南角炊事班的巷口,一路沿着平房门前走。就是这一条不起眼的沙土路,我记忆深刻。路的右侧是一片工建连的营房,且都是平房,显得低矮、局促、寒伧。工建连的战士好像一天到晚都是穿着脏乎乎的军便服,像个民工。工建连南边是一片菜窑,二连的菜窑也在这里。我多次下到菜窑里面搬运大白菜,看着一颗颗大白菜躺在一层层简陋的用粗糙木头搭起的铺子上,当时也感到很新奇。再往前走,就是几棵粗大而孤零零的柳树。当月色朦胧,我与张玉强背着步枪行走在这片空旷的天地里,看着周遭隐隐绰绰的夜色,除了不知名动物的鸣叫,就是彼此一前一后的脚步声。这种景像,在我的脑海里沉浮多年,挥之不去。
在七班,我经历了当时海军大院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黄楼北面仓库火灾。时间大概是在1981年初的一个晚上,当时天气比较冷,至于什么原因起火已不得而知。现在只是隐约记得全班战士拿着脸盆去扑火。我们从露天的水池龙头里接水,再冲进火海把水一盆一盆扑向火苗。仓库里大多是书等印刷品,尽管战士们奋勇灭火,但结局是一切化为乌有。灾后,连里统计战士脸盆损失情况,我也因此领到一个新的脸盆。脸盆是瓷的,底部有几朵艳丽绽放的牡丹花,“花好月圆”四个字格外夺目。
火灾后的一天上午,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连里派我到火灾现场值勤,值勤点是在通信楼东侧,任务是不让闲散人员进入火灾现场。那天天色阴沉,天空被灰色的云朵裹挟着显得沉闷。眼前是一片熏黑的断壁,烧焦的杂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这时,有一位老人走到我旁边。他花白头发,寸头,圆脸,目光炯炯,精神矍铄,身穿海军棉大衣,双手插在衣兜里。他环顾火灾现场后就径直向纵深走去。
“同志,请您不要往前走。”我很礼貌地对老人说。
“我是梅副司令。我可以进去。”老人淡然地瞥了我一眼,边说边继续往里走。
梅副司令?我心里一楞:自己是个新兵蛋子,又没见过梅副司令,能怎么办?只能是注视着他默默地向前走去。
回到班里后,我把当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其他战友。他们说梅嘉生副司令员就住在海后小院,离我们二连很近,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是海军的老领导。听了大家的一番话,我对梅副司令肃然起敬。
80年代初的军营生活比较单调,看电影算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事,那个时候主要是看露天电影。当时看露天电影有两个地方:海后广场与大院的大操场,但更多的是在大操场看。大操场在海军大院的中心位置,那时的大操场是一片沙土地,光秃秃的,每当风沙刮来,整个操场尘土飞扬。大操场主要是机关干部战士军事训练、居民锻炼身体与娱乐的场所。操场的北边是海军俱乐部,俱乐部有一个很大的舞台。舞台朝南,面对大操场,但不知为何舞台被封闭了,仅在舞台边缘留下约三米宽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警卫二连战士看电影的固定场所,不知是约定成俗还是什么原因,每当晚上看电影,战士们就从西边的舞台台阶拾级而上,全连战士整齐地坐在小马扎上,无人相争。2006年国庆,我故地重游,专门到大操场转了一圈,发现已变了模样:画了红色跑道,栽种了碧绿了草坪,现代气息比较浓厚,但大的格局没有改变。
在七班,青春年少的我也写了一些青涩的朦胧诗,当时主要描写两个主题,一个是对越自卫还击战,歌颂革命英雄主义;另一个是赞美青春。我每次写好稿子后就交给文书武海珍,由他把稿子送到俱乐部。中午就餐前,全连战士在连部前集合唱歌,此时经常从食堂的喇叭里飘来广播员清脆悦耳的声音――“下面请听诗朗诵……作者警卫二连战士某某某”,每当听到这个名字,内心为之一颤――那是一种激励。
1981年初,我与连里几个战友参加海军俱乐部组织的一个书画创作课,授课的是范曾和刘柄森两位大师。范曾是国学大师、书画巨匠,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以诗为魂,以文为骨”的美学原则,在后来国内诸多书画活动中出镜率比较高,也因此而一直牵动我的视线。在海军俱乐部授课现场他用白描的手法画了几幅人物画,其中一幅是李白醉酒。刘柄森是著名的书法家,隶书艺术成就最高,闻名于世。后来我在练习书法时就按照其要求临摹学习。这两位大师对提高我个人书画鉴赏水平起到了启蒙教育作用。
在七班,脑子里还残存着下面一些碎片:
排里组织了一次到颐和园游览,在我的相册里,留下了在警卫二连仅存的几张珍贵的黑白照片。合影照都是与三排几个战友,现在已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了,熟悉的只有一张与三排长佘生俭和一张与陈国京的合影。
我与战友们还到北京展览馆前的马路旁种树。记得种的树离展览馆很近,就在展览馆的西北方向。种的树是从其他地方移植过来的,树径比较大,但叫不上树名。如果这些树现在还在,已是参天大树。
我与战友们到丰台区岳各庄参加过生产劳动。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与战士们在水田里干活的情景……,后来驱车到一个菜圃,拉着菜苗去种菜。
我还与战友们在清晨经常到复兴路人行道扫树叶,从翠微路口一直扫到公主坟转盘前;还到1路与4路车站打扫卫生……
大概在1981年的春末夏初,我从七班调到连部担任通信员。当时的连长是翟永福,副连长孙锡忠,后来三排长刘业勤提拔到副连长;指导员是李维良,副指导员高金昆;一排长金马良,二排长谢渡云,三排长佘生俭,司务长赵和生,公务排排长郑智昌,警卫室排长陈建太。连部班成员有军械员牟善铸,卫生员李贵科,文书开始是武海珍,后来是杨纬富,后勤是丁忠毅、徐世坤。对连部班战士的称呼都是在其姓前冠“小”,显得亲切,我姓王,别人就叫我“小王”,牟善铸就叫“小牟”。
通信员除整理连部内务外,还要收发报刊、信件与包裹,还要替战士到翠微路邮电所取汇款,到万寿路邮电所取包裹;取汇款、包裹前要到队列值班室盖章。
在此,有必要介绍我第一次到队列值班室盖章的情景。
队列值班室在黄楼一层。海军大院的黄楼分主楼与配楼,六层高,其中主楼七层高,绿色琉璃瓦顶,怀抱粗大廊檐圆柱,飞檐斗拱,气宇轩昂。那是1981年的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当我一踏进黄楼的刹那立刻感到凉爽宜人,沁人心脾。但我不知道队列值班室的具体位置,就走到了左边的海司政治部,问一个秃顶的海军军官,他很客气地用手指点着告诉我队列值班室在什么地方。可谁能知道,黄楼在我人生的履历上刻上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后来在此工作与生活了近10年。
刚到连部时,发生一件有趣而又尴尬的事。我是浙江人,南方口音较重,普通话不标准,有一次,军务处李兰煜参谋来电话找翟连长,我就把电筒撂下,去外面找连长。连长从家属房方向走过来。
“连长,你的电话。军务处李参谋打来的!”我对连长说。
“谁打来的?”连长没听懂我的话,反问了我一句。
“李参谋!”我很认真地复述了一遍。
“谁打来的?”连长还是没听懂我的话,再次反问我。
“李——参——谋!”我也很认真地一字一句再说了一遍。
连长口中念念有词,带着慈祥而微微的笑容,虽然身材略显富态,但魁梧不失步履矫健,那憨厚可掬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2017年,萧山战友见面会时惊闻翟连长、李维良指导员去逝,我内心悸恐:两位尊敬的老首长离开了我们!
关于翟连长,还有一个场景值得一说:大概在1981年秋天,翟连长组织战士扩建家属房。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在场的有一个叫张阿根,他墙砌得很好,听说在家里就是一个泥水匠。翟连长表扬了他。那天艳阳高照,战士们的脸上都绽放着笑靥,洋溢着青春与活力。战士们就在这样的氛围里,站在脚手架上愉快地与连长一起砌墙。不知为何,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建筑工场,而且是一幅画,是一幅生动的画。可惜我不是画家,否则,我会把这场景用画笔记录下来,题目就叫《连长与战士们一起劳动》。
在连部,与战士们相处得都非常和睦。牟善铸比我年长几岁,参军也比我早,他像老大哥一样关照我、帮助我。刚到连部那阵子,我还不会骑自行车,就是在他的悉心呵护下很快就学会了。我们从连部到一排前的这块空地上学习椅车。我双手握着车把,他在后面帮我掌握平衡,防止跌倒,就这样来回地练习。有一次,军务处的刘振山参谋到连里来检查工作,笑咪咪地看着我:“小王进步很快嘛,会骑了!”当听到这样激励的话,心里乐滋滋的!
牟善铸是军械员,军械库在连部对面,有几次他叫我一起在库内擦枪。军械库室内没有窗户,门关上屋子里黑乎乎的。昏黄的灯光显得乏力而黯淡,我们像似跺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有一次擦枪时发现墙角一个麻袋,撕开才知是核桃。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物质匮乏,生活不富裕,我在老家从来没有吃过核桃,再说也不种植核桃。小牟从麻袋里取出一些核桃叫我吃,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到核桃。
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才明白,二排与三排的房前,东边靠大院围墙的路旁全是核桃树。随着夏天的到来,嫩叶渐渐地变成了茂盛的技叶,树枝向四周伸展,就像一把巨大的绿伞。到秋天时,树上挂满了核桃,恰似一盏盏碧绿的小灯笼。这些核桃怎么摘下来的已不得而知了,只记得青青的一层核桃晒在连部东边的路旁……但我没有吃过这些核桃。
那时,二连在卢沟桥有一片自留地,我也多次参加在那里的生产劳动。记得主要是种植地瓜。不知是连里吃不完还是什么原因,地瓜丰收的时候,连部几个战士不时去大院卖地瓜。记得我与李贵科、牟善铸都拼过卖地瓜的伙计。我们骑着装满地瓜的三轮车,一般都从营区东南角炊事班边上的巷口出发,经过警卫一连门口,穿越雄伟厚重的灰楼拱门,到达了灰楼区。灰楼是一组建筑群,是海军大院机关干部家属楼群,因为它外观是瓦灰色的,由此得名,分别由100号、200号、300号、400号楼四座楼组成的一个方形,中间一个宽大的庭院。记得当时庭院内还有防震棚。
“卖地瓜啦!”小李与小牟对着楼门喊。声音虽不很响亮,但似乎特别有穿透力,清脆而有力。叫卖声透过冬日清冽的空气弥漫在庭院上空。
有些老太太、老爷爷就会巡着声音出来买地瓜。不过当时卖多少钱一斤已经忘记了。
我们从灰楼出来往南,路过高坡仓库、灯光球场、第一招待所、游泳馆、七一小学往西,最远到海军文工团……那一路走过的光景,如今时时浮现,恍如隔世。人生就是这么奇怪,走过的路不管是短还是长,经历的事无论是和风细雨还是风雷急荡,只要是把心融入进去了,那留在脑海里的就会经久不忘。
在担任通信员的日子中,我与孙锡忠副连长建立起了一种深深的难以名状的情感,敬仰也好,崇拜也好,总之是兼而有之。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1982年5月,我调离了警卫二连,此后就没有见过他。在离开警卫二连时,当时自以为是地告诫自己,努力工作,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以不同的面貌向这位领导汇报自己的进步。调到机关后,我多次路过警卫二连大门口时都想见一见这位老领导,但又鬼使神差地一次次被自己刻意、残忍地否定了。就这样,一江春水向东流――过去了35年。至于其中有着怎样崎岖、痛苦的心路历程,时至今日,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就随风而去吧。
2017年在萧山举办第一次战友见面会,我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见到孙连长与嫂子身体棒棒的,生活得很甜美,我释怀了。衷心祝福孙连长全家幸福永远……
聚也匆匆,散也匆匆。警卫二连只是我人生长河里飞溅的一朵浪花,非常短暂,但这段时光的积淀镌刻在我的心头是恒久的。
岁月静好,想起大家,满心温暖;阳光微淡,一路走来,最美的风景,不是春花秋月,而是当初在警卫二连时藏在心灵深处的那份傻傻的纯真。守着剩下的流年吧,生活安稳,平平安安过好每一天……
最后,我要感谢与二连每一位战友的相遇,因为你们,让我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因为你们,让我的回忆变得缤纷绚烂。
今年是我参军4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满怀感慨地写下这些文字,除了纪念自己生命中这段难忘的青春岁月,也把此文敬献给曾经与我“同训练、同学习、同劳动、同休息,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的原海军司令部警卫二连全体指战员。
( 2020 年 6 月 3 日 于浙江温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