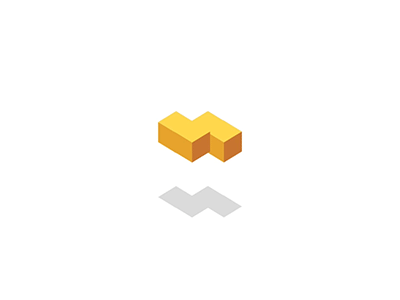原来工作忙,很少回家乡;现在退休了,却又忙起天伦之乐。家乡的老哥们一句话:“山猴子,你真的把家乡忘了吗?该来看看我们这些快要入土的老哥们了呃!见一眼就少一面哦!”这喊着小名,带着情绪和埋怨想念地对我说。于是,我决定独自回家乡一趟。
坐在驶向“南山背”的班车上,透过车窗的山山岭岭,似乎一见如故。我轻轻叩问自己,家乡是什么?这口头禅的叫词,突然在我大脑尽是一片空白。家乡,多少年的时光,多少有趣的记忆,仿佛被城市的脚步甩得太远太远。
翻过凤凰山,到达漩涡镇。换坐通村面的,越过几道梁,在滴水崖下的塞牙砭停下,因为没有公路了,只有徒步前行。真的多年没来过这里,几乎忘记这山间小路是又陡又窄,曲里八拐是要攀爬的。十多里小道上,泥石路上留下一个个浅浅的鞋迹,尘土上汗水扎出一个个淡淡的窝痕,两耳却有久违未闻的一啾啾清脆鸟语,双目惊艳着清风吹过的一座座葱郁青山,一个多小时的经历,才慢慢理解到家乡二字的意思。
这种体验,让我想起初到城里,人们叫我“老朳人”的名号,家乡的窗口一下豁然打开。一面坡还是连着一面坡,山坡已是花草树林盖顶,坡顶下依然是长庄稼的坡地,我似乎回到了生命开启的源地。一条小溪还是隔着一条小溪,溪水比过去更汪势、更清亮地涌向汉江,我仿佛触摸到了身上流动的血脉。家乡到了,让我产生不尽的遐想。过去虽然土地很贫瘠,却丰富了我的情感;那时虽然劳作很艰辛,却厚实了我的历练;儿时虽然日子很困苦,却磨砺了我的品行。这片土地,这一方父老乡亲,给了我一生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快到陈家垭子的茶树包,我见到陈兴良老哥,一副压弯扁担的苞谷坨子在他肩上担着,他前面是一个背着大过身子背笼的孩子。“好稀客哦,你真的回来了!”说着他放下担子,又向前面喊叫:“佩娃子,歇会儿,你陈爷爷回来了。”佩娃子认不得我,直愣愣地瞅着我。他闪动着两颗亮晶晶的眼珠,是清澈的目光,红坦坦的脸蛋饱含土地的滋颜,从他的神态我看到了生命本质的原色。“一定先到家坐坐!”良老哥立马挑起担子,佩娃子也背起背笼,那前行的脚步很溜刷‚。走在这枞树砭的路上,我直喘着粗气,想给佩娃子帮忙的客气话,都没能说出口。砭子路上,乱石茬子把脚心锥得矜痛ƒ,而我心里更难受的,是不知啥时,抹掉了自己渭子溪水一样的坚韧和青石崖一般的刚毅。烦躁、脆弱、冷淡如流行性感冒一样传染了城镇的角落,我也没能逃掉。与良老哥爷孙俩同行,让我深深感受到家乡的含义。
立在砭子上看陈家垭子,看得清飘摇着的缕缕炊烟,能听得见此起彼伏的晌午鸡鸣。刚踏上院坝坎,“汪,汪汪……”几声迎主归来的狗叫,把我和家乡拉扯得亲昵而绵缠④。良老哥住陈家垭子正东,土墙瓦房三大间,堂屋中间一个大四方桌,墙东边摆一副手推磨,西墙边烧的疙瘩火熏着腊肉。“你良嫂子已经去世几年,佩娃子爸妈也外出打工多年了,家里就剩下我们爷孙俩”良大哥一边诉说,一边向门外喊:“山猴子回来了——”。不一会儿,垭子人挤满一堂屋,亲热喜气的话堆满了整个垭子。良老哥说,请客不如遇客,那就吃一顿大锅饭。说起大锅饭,那是家乡大集体时最热闹的时候,我就喜欢坐在大灶前,往灶洞里添柴火,听毕剥嚓啦的声响,看那燃烧的柴火,释放出生命最后的能量。大灶堂做出的米饭,为什么那么喷香、那么爽口、那么惬意!是今天红堂堂的柴火,敞亮了我淤塞已久的心绪,才感悟到那是生命煅烧的结晶。
乡亲们土灶前挂一串串香肠,堂屋疙瘩火上熏一排排腊肉,这是家乡炊烟的味道,更是家乡草木生命的温度!当良老哥端上一碗苞谷米饭,那清香直窜鼻窟窿,我的吃相,把乡亲们惬意的笑塞满整个屋子。他们伸出的一双双手,老茧、冰裂、粗糙,好像一把把钢锯,割裂着我那温文尔雅的情调。尤其是已近80岁的谭叔,那一串白胡须,似一根根银针,质朴而坚韧的扎向我患有城市病的穴位。我终于明白了,家乡人生命的蓬勃,正是他们的根养植在大地的沃土!
生命浇灌着我成长,因为山那边有我的家乡;乡村供养着城市的心灵,城市唤醒梦中的游子回乡;乡土柔化着现代文明的硬度,滋润成一幅田园美景贴在城市记忆里。家乡就那样,有飘不完的炊烟,流不干的河床。
注:汪势:土语,形容水势比较大。 ‚溜刷:方言,快速、利索; ƒ矜痛:土语,很不是滋味的疼痛。 ④绵缠:土语,关系密不可分。